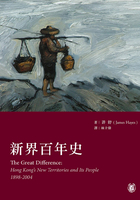
自序
如果有位在新界出生的百歲老人從海外回鄉,看到今天業已十分都市化的新界,大概認不出這就是自己成長的地方了。那些在1898年改受英國統治的農村居民的後代子孫,儘管已被數目比他們高出許多倍的外來人口所淹沒,卻仍然保留自己的家園、傳統和特色。想到香港在戰後現代化步伐之快和程度之大,這是怎麼做到的?尤其是那些祖先不巧住在這塊租借地中稱為「新九龍」地區的人,面臨的命運迥然不同,更不必說那時候數目眾多的本地水上人的後代?(1)本書以英國租借新界時期的香港歷史大圖景為背景,着重述說他們在這百載變遷中的故事。
我撰寫關於新界的事情,始於四十多年前,當時較少這種著述出版,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尚有未竟之業。時至今日,大量資料已唾手可得,這些資料源於在村落所做的原創研究、在地方上蒐集的文獻,以及口述歷史。但是,這些著述(包括拙著)大多局限在狹窄的範疇,而我寫此書的目的,是要提供較為廣闊和十分不同的視野。
如同之前發表的著述,我寫作時有兩副面孔,撰寫此書時尤其如此:一方面戴着政府官員的眼鏡,運用我的經驗去看事物,但我還有另一副歷史學家的眼鏡,令觀點更為平衡。在這方面,我注意到一位評論家的觀察,他評述我那本回顧公職生涯的回憶錄時說,(2)我囿於自己的觀點而無法跨越。考慮到這句話的重點在於什麼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儘管我對此評語不完全同意,但仍念茲在茲,彌自儆惕。
我對於老派鄉下人和昔時的生活文化深懷好感,這點在此書清楚可見,但撰寫此書的目的,並非為偏幫獨厚原居民。原居民的記錄中充滿矛盾和不一致,他們既親切又不友善,既樂於合作又常蓄意刁難,既彬彬有禮又橫蠻粗野,既視錢財和私利如命,又可以為了公益不吝付出時間和金錢等等。畢竟他們和你我一樣,皆是凡人:儘管這點再明顯不過。但是,他們性格中美善的一面,是恆久而真實的,他們的成就也舉足輕重。我有幸能與許多秀異之士共事合作,當中少數人與我相識甚久,成為莫逆之交,我感到十分榮幸。
若沒有許多男女耆宿的協助,本書是不可能寫成的,他們把自己的生活細節,尤其是早期歲月的事情,不憚其煩告訴我,又樂於為我釋疑,我對此銘感五內。另外,將他們介紹給我認識,並協助安排探望和訪談的朋友,我同樣感激不盡。在香港,溫安和楊百勝尤其一直鼎力協助。
我還要向同行的作者和研究者致敬。許多年來,香港(尤其是新界)一直極其幸運獲他們青睞。他們無疑都和我一樣,發現古老中國農村社會和它向現代的過渡有特別引人入勝之處。無論是什麼原因,詳盡的研究所在多有,可供本書參考。我從中獲益的研究有許多,要選出一些十分困難,但約蘭·艾默(Göran Aijmer)(3)、裴達禮(Hugh Baker)、陳永海、科大衛(David Faure)、夏思義(Patrick Hase)、詹森(Graham Johnson)和羅碧詩(Betsy Johnson)、彭文浩(Michael Palmer)、蕭國健、華琛(James Watson)和華若璧(Rubie Watson)的研究,我一向覺得甚有幫助。(4)在更為近期,我的朋友高添強為我帶來靈感,尤其是關於他的鄉村——東九龍牛頭角客家採石工人從前聚居的村落,該地屬於1898年租借地的一部分,為了發展該區,我在1966年奉命清拆這條村。(5)對於所有這些朋友和許多其他人,我都在此致以謝忱。(6)
我須再一次深切感謝內子黃超媛的包容,每次我在埋頭苦幹撰寫歷史時,她都會展現這種包容。我開始寫另一本書時會是什麼光景,她十分清楚,並永遠給我支持,這是完成這本書所不可或缺的。我在悉尼的摯友瑪麗安·福特(Mariann Ford),在英國的彼得和艾琳·威廉斯(Peter and Irene Williams)再次幫忙閱讀初稿,並提供寶貴意見。另外還有鄧恩(R. Ian Dunn),我這位朋友總是樂於助人,而且是一切與攝影有關事情上的魔法師。完成這本書的旅程,一如以往既崎嶇又漫長,全靠這些人沿途幫助,我才能內心踏實地將之走完。我尤其欠瑪麗安的人情,她總是很有興趣讀我的書,無論是此書還是之前的著作,而且願意在各個階段仔細地提出洞中肯綮的評語。
我還要感謝香港歷史檔案館的許崇德,他對於我要查閱文件或資料的請求,一直鼎力協助;還有香港大學出版社社長戴高賢(Colin Day)博士,他提出令我深獲教益的鼓勵,而且是個穩健的掌舵人!我也感謝十分能幹的編輯陳粹華,以及港大出版社製作團隊自始至終的大力幫忙。
本書使用的圖片,來源已在圖片說明中標出,在此向相關各方致謝。圖二、十二和十九是來自艾思滔(Edward Stokes)的《逝影留踪:香港,一九四六——四七》(Hedda Morrison's Hong Kong: Photographs and Impressions 1946-4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原圖底片藏於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在此對艾思滔的協助致謝,還要感謝賴恬昌先生惠賜墨寶,令標題頁大為生色。
寫畢此書初稿後,我看了陳偉群的研究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發現他也強調香港舊轄地與1898年新獲領土之間的差異。他說:一個有着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社會結構,另一個則已經穩固建立了商業經濟、殖民政府,以及多種族雜居的社會(第16頁)。他之後補充說:「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今天的香港島和新界無疑已成為單一、不可分割的整體,但調查此融合過程會很有趣味,是很值得探索的課題,需要非常不同的研究。」(第17頁)雖然我撰寫此書,完全是源於駱克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說話,但也希望此書對於達成陳博士的目標也略有幫助。
此書會被人視為內部人士的記述,書中內容所依據的基礎,是我任職政府和長期研究歷史所得的知識和資料。此書旨在提供一個梗概,冀能對其他研究者有所裨益,因此書中列出大量參考資料,偶爾還有長篇註釋,這是由於在導論和內文各處提出的主題,以及層面更廣泛的問題,還有待來者花更多工夫去探討。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村民從收地發展的現金補償、換地權益書、鄉村搬遷和丁屋政策所得的經濟利益,我在此書沒有試圖估計這種利益;對於日後研究這點的人,我只想提醒一句,那些沒有因為公共建設而徵收私人土地的地方,是得不到這種利益,也不是所有人都得到這種利益的。
雖然書中各章全是各自獨立,為了便於閱讀,註釋原本打算採用腳註方式,但因為註釋篇幅頗長造成問題,現改成尾註放在書末(中文版改用腳註形式—編者)。在註釋以外,本書是以一般讀者為對象,尤其是與香港有關連,或對這個地方和居民感興趣的人。如同我的其他著述,撰寫此書的辛勞,我甘之如飴,盼能稍為回報香港帶給我的一切。
許舒
2006年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