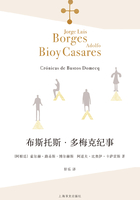
第3章 与拉蒙·博纳维纳一起度过的下午
一切统计数据,一切单纯的描述性或信息性的工作,都是以那个璀璨却可能不理智的希望为前提的,那个前提便是,在广博的未来里,类似我们这样但比我们更清醒的人,会从我们留给他们的数据中,推断出某个有用的结论或某段令人钦佩的概括。遍览过拉蒙·博纳维纳的六卷《北—西北》的人可以不止一次地依靠本能察觉到,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更确切地说,存在这么一种需要,在未来一起完善和完结这位大师所奉上的作品。我们得赶紧提醒一下大家,这样的思考完全是个人行为,绝不是博纳维纳所授意的。有人认为,这部他为其奉献一生的作品实现了美学或科学的超越,在我唯一一次与他的对话中,这位先生完全否定了这种观点。时过多年,就让我们来回忆一下那个下午吧。
一九三六年左右,我在《最新时刻》的文学增刊工作。当时主编的兴趣点也包括文学议题,于是便在一个寻常的冬季礼拜日派我去小说家位于埃斯佩莱塔的隐秘居所做采访,那时他已小有名气,只不过还没到特别著名的程度。
他的家直到现在都保存得很好,那是一栋平房,屋顶平台上突兀地立着两个带栏杆的阳台,可悲地显示着预先设计好的更高一层。是博纳维纳本人给我们开的门。他戴着茶色眼镜,就是他流传最广的那张照片上所戴的那副,看起来像是在呼应某种暂时的病痛,对他的轮廓也没有起到任何修饰的作用,他的脸颊很宽很白,五官都像是被隐去了。这么多年后,我能记起的,大概还有一条麻布罩袍和一双土耳其便鞋。
他的礼貌很自然,但也没能掩饰住他的戒备心;最开始,我以为那都是拜谦逊所赐,但很快就明白了,这位先生非常自信,正在不紧不慢地等待众人一致将他推上神坛的时刻。他一直坚持着高标准严要求且无穷尽的工作,所以在时间上很吝啬,几乎,或者说根本就不在乎我为他提供的广告宣传。
他的办公室里——那儿有种乡间牙科诊所候诊室的感觉,挂着蜡笔海景画,摆着牧人和狗的陶瓷像——书很少,最多的是各行各业以及各个学科的词典。再提一句,书桌的绿毛毡垫上的高倍放大镜和木工尺也并没有让我感到意外。咖啡和烟不断刺激着我们的对谈。
“很显然,我读了很多遍您的作品。不过,我认为,为了让普通读者、让大众能相对更好地理解这部书,您最好能用综述精神来笼统地概括一下《北—西北》的酝酿过程,从最初的细微念头到最终的长篇巨著。”我有点儿胁迫他的意思,“从头道来,从头道来!”
一直没有表情的灰色面孔在那一刻有了神采。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倾泄而出的精炼话语。
“最开始,我的计划并没有超出文学范畴,甚至没有超出现实主义范畴。我所渴望的——说起来也不怎么特别——就是写出本土小说,很简单的小说,塑造一些人物,讲述大家所熟知的反对大庄园的抗争。我想到了我的镇子埃斯佩莱塔。我当时对唯美主义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只想对当地社会的某个特定方面做出一种很诚恳的见证。最先把我拦住的困难是那些琐碎的细节。比如人物的名字。如果把他们现实中的姓名安在人物身上,就要面临诽谤指控的风险。办公室就在附近的加尔门迪亚博士是个戒备心很强的人,他曾经很肯定地告诉我,埃斯佩莱塔的普通人都很爱找麻烦。不过,还可以编名字,但这就相当于对虚构敞开大门。我于是选择了大写字母加省略号的形式,只是这个办法最终也没能让我满意。随着对主题的深入,我明白了,最大的困难并不是给人物命名;而是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我怎样才能钻进我邻居的脑袋里?怎样才能在不舍弃现实主义的情况下猜出其他人的想法?答案很明白,但是最开始我并不想看到它。我调整目标,瞄准了写出一部家畜小说的可能性。但是怎么才能用直觉去感知一条狗的大脑运作呢?怎么才能进入一个视觉弱于嗅觉的世界呢?我有些晕头转向,撤退到了自我里面,觉得除了写自传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但那儿也有座迷宫。我是谁?今天的我,是否头晕目眩?昨天的我,是否已被忘却?明天的我,是否不可预见?还有什么是比灵魂更不可感知的?如果我为了写作而监视自己,这种监视会改变我;如果我放任自己自动写作,那么我就是在放任自己的漫无目的。不知您是否记得那件事,我想应该是西塞罗讲的吧,说的是一个女子去一座寺庙寻找一道神谕,在不知不觉间说出了一些词句,其中就包含了她自己所期望的答案。在埃斯佩莱塔,我身上发生了类似的事。我重读了自己的笔记,倒不是想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而是想去做一些事情。我要找的钥匙就在那里。就在某个有限的领域这几个字中。我写下它们时,所做的只不过是重复一个稀松平常的比喻;而重读它们时,某种启示让我惊异不已。某个有限的领域……还有哪个领域是比我办公的松木桌的一角更有限的呢?我决定局限于那个角落,局限于那个角落有可能展现给我的东西。我用这把木工尺去量——您可以随意检查——桌腿,证实了桌面位于离地面一米一五的高处,我认为这个高度很合适。再往上不断升高,会有碰到房顶、屋顶平台的风险,很快还会到达天文学所涉及的高度;向下,要是不陷入地球内部,我便会沉入地下室,或者到达亚热带平原。除此之外,那个被选中的角落所呈现的都是有趣的现象。铜质的烟灰缸,还有双头铅笔,一头是蓝色的,另一头是彩色的,等等。
说到这儿,我便按捺不住打断了他:
“我明白,我明白。您讲的是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都了解那个烟灰缸:它的铜质色调、特定重量、直径,铅笔和桌子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标志的设计、工厂价、零售价,以及其他不仅恰当而且严谨的数据。谈起那支铅笔——那可是一支金辉柏873啊——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您发挥您的概括天赋把它压缩在八开二十九页纸上了,哪怕是最难以满足的好奇心都不会再渴望了解更多东西了。”
博纳维纳并没有脸红。他不紧不慢地开始重新掌控那场对话:
“我看,种子并没有落到犁沟外嘛。您已经吃透我的作品了。作为奖励,我赠送给您一个口头附录吧。它涉及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创作者的疑虑。把通常占据书桌北—西北角的物品记录下来是一项赫拉克勒斯式的任务,我花费了两百一十一页的篇幅来记述这项工作,它一完成,我便自问更新存货是否合适,这里说的是专断地引入其他物品,把它们放置在磁场中,废话不说地开始着手描述它们。这样的物品,不可避免地被我的描述任务选中,从这个房间,甚至这栋房子的其他地方被带来,不可能像最开始的那些物品那样自然、自发。然而,它们一旦被放置在那个角落,就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就会呼唤一种类似的待遇。道德与美学的短兵相接!这个难题被面包店派送员的出现解开了,那是一个完全值得信任的年轻人,虽然有些笨拙。我们提到的这个笨人扎尼凯利,按俗话说,到这里是来做我的天外救星的。他的迷糊帮我做了结。怀着带有恐惧的好奇心,我像渎神的人一样,命令他在那个已经空了的角落里放上东西,任意什么东西都可以。他放了一块橡皮、一支自动铅笔,又重新放上了那个烟灰缸。
“著名的贝塔系列!”我突然大叫,“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像谜一样的烟灰缸的回归,您用了几乎同样的语句进行重复叙述,只不过这一次还提到了自动铅笔和橡皮。不止一位肤浅的评论家认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失误……”
博纳维纳插了话:
“我的作品里没有失误。”他带着完全合理的庄重态度声明道,“对自动铅笔和橡皮的提及就是十分有力的标志。在一位您这样的读者面前,去详细描述之后放置的种种物品是没有用的。只需说明,我闭上了双眼,任那个笨人在那儿放上一样或多样东西,之后就上手写作!理论上,我的作品是无穷无尽的,实践上,在处理完第五卷第九百四十一页[6]后,我恢复了自己休息的权利——您就称它为中途小憩吧。”在除此之外的地方,描述主义一直在蔓延扩张。在比利时,人们正在庆祝《水族馆》的第一稿,我想,这部作品在提醒人们去注意那不止一种的异端邪说。在缅甸、巴西以及布尔扎科也都出现了新的热点。”
不知怎么,我感觉到采访已经接近尾声。为了给告别做铺垫,我说:
“大师,在走之前,我想最后再请求您一件事。我可以看一眼作品中写过的某样东西么?”
“不可以。”博纳维纳说,“您看不到。每一件放在那儿的物品,在被下一件取代之前,都被很严格地拍摄了下来。所以我得到了一套非常棒的底片。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它们都被毁掉了,我当时真的很难过。物品原件毁掉的时候我就更难过了。
我顿时沮丧起来。
“怎么?”我甚至有些结巴,“您怎么敢毁掉θ黑棋的象和γ锤的锤柄呢?”
博纳维纳悲伤地看着我。
“牺牲是必要的。”他解释道,“作品就像成年的孩子,得靠自己活了。保留原物会给它带来不合宜的核对比较。评论会被诱惑、挟持,以作品是否忠实于原物的标准来评判它。这样我们会落入唯科学主义中。您应该很清楚,我否认我的作品只具有科学价值。”
“当然,当然。《北—西北》是一种美学创造。”
“这是另一种错误,”博纳维纳做出了判定,“我否认我的作品只具有美学价值。这么说吧,它有自己的地位。所有被它唤醒的情绪,眼泪、掌声、鬼脸,这些我都不在乎。我并不想去教导、感动、娱乐他人。这部作品走得比这些更远。它同时渴望最卑微与最崇高的东西:它就在宇宙某处。”
他把坚固的脑袋缩进肩膀,没有再动。眼睛也不再看我。我明白拜访已经结束,便尽快离开了那里。余下的只有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