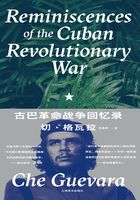
第7章 叛徒的下场
这支小小的部队重新集结以后,我们就决定离开埃尔洛蒙山一带,转移到新的地区。一路上,我们继续和当地的农民保持频繁联络,为我们的生存打下必要的基础。与此同时,我们准备离开马埃斯特腊山区,向平原方向前进,与组织城市工作的同志会见。
我们经过了一个叫拉蒙特里亚的村子,随后就在一条河边的一小片树林里扎下营来。那地方属于埃皮法尼奥·迪亚斯的庄园,他的几个儿子加入了我们革命队伍。
我们决心在“七·二六运动”内部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因为我们游击生活的这种流动性和秘密性使“七·二六运动”的两派之间无法交往。实际上,这是两个独立的游击团体,有着各自不同的战略战术。当时并没有出现像随后的几个月中那么严重的危及“七·二六运动”团结的裂痕,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彼此之间有分歧了。
我们在这个庄园里会见了城市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其中有三人是今天全古巴都熟悉的妇女:比尔马·埃斯平,现任古巴妇女联合会主席,她是劳尔的妻子;艾德·圣玛丽亚,现任“美洲之家”主席,她是阿曼多·阿特的妻子;以及塞莉娅·桑切斯,这位敬爱的女同志在斗争中始终关心我们,后来为了支持我们,加入了我们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游击队直至战争结束。另一个来访我们营地的是福斯蒂诺·佩雷斯,他是“格拉玛号”上的我们的老相识了。前阶段他到城市去执行任务,这次是回来向我们汇报工作,然后,还要返回城市执行任务。(不久,他就被捕了。)
我们还在这里会见了阿曼多·阿特,我还有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来自圣地亚哥的伟大领袖弗兰克·派斯。
弗兰克·派斯是一见面就令人肃然起敬的那种人。当时他看上去多少就像我们今天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模样,不过一双眼睛更显得异常深沉。
我和弗兰克·派斯只见过一面,后来他就牺牲了。今天让我来谈谈这样一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民的同志真有些为难。我只能说,他深沉的目光显示出他全心全意忠贞不渝地投身自己选择的事业,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才。今天,人民称他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弗兰克·派斯”。我虽然只见过他一面,但我看这种赞誉是名副其实的。许多同志如果不是早年遇难的话,今天就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事业中冲锋陷阵,弗兰克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牺牲是人民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付出的沉重代价的一部分。
弗兰克的牺牲为我们在执行命令和加强纪律方面上了无言的一堂课,它警示我们擦去枪支上的尘土,清点好弹药,精心装箱,防止丢失。从那天起,我就下决心更加小心地保管好我的枪支(虽然自己确实这样做了,不过我还不敢说自己是个一丝不苟的模范)。
在这片小树丛里我们也见证了其他一些重大事件。我们第一次在这里接受了一位新闻记者的采访,而且还是位外国记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赫伯特·马修斯[3]。采访时他随身只带了一个简陋的方镜箱照相机。他就是用这架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在全球媒体间广为传播。巴蒂斯塔政府的一名部长还多次愚蠢地发表声明,对这些照片大加质疑。采访时的译员是哈维尔·帕索斯[4],他后来加入了游击队,并在游击队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
采访时我并不在场,据菲德尔说,马修斯单刀直入地问了许多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刁钻的问题,他似乎很同情我们的革命。在被问到是否反对帝国主义时,菲德尔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还说他反对美国向巴蒂斯塔政权运送武器,他坚持认为这些武器并不会用于北美大陆的防御,只会用来压迫人民。
当然,马修斯的采访时间很短。他刚走,我们就准备转移。不过,有人提醒我们要加强警卫,因为欧蒂米奥就在这一地区活动。阿尔梅达随即接到命令,立即查明欧蒂米奥的下落,将他抓捕归案。胡利奥·迪亚斯、西罗·弗里亚斯、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都加入了巡逻搜索队。西罗·弗里亚斯没费多大周折就抓到了欧蒂米奥,把他押送到我们这里。我们在他身上搜出了一把0.45英寸的小手枪、三颗手榴弹和一张卡西利亚斯签发的安全通行证。一被抓,又铁证如山,欧蒂米奥也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扑通一声便跪倒在菲德尔面前,说他知道自己该死,只求我们把他杀了算了。他似乎一下子衰老了许多,鬓角不知不觉地长出了不少白发。
当时气氛格外紧张。菲德尔严厉斥责了他的变节行为,欧蒂米奥知道自己十恶不赦,只求一枪把他了结。我们谁也忘不了欧蒂米奥的最好的朋友西罗·弗里亚斯对他的控诉。他让欧蒂米奥好好想想自己为他所做的一切,好好想想他和他的兄弟是怎么照顾他一家的。西罗·弗里亚斯历数了欧蒂米奥的叛变行径,他先是害死了西罗的兄弟——西罗的兄弟就是被他送交到政府军手里,几天前刚被杀害——后来又想方设法摧毁整个游击队组织。这是一次长时间的慷慨激昂的愤怒声讨。欧蒂米奥低垂着头,一声不响地听着。当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时,他说希望革命,更恰当地说,希望我们这些人今后照顾好他的孩子。
革命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尽管欧蒂米奥·格拉的名字今天在本书中又出现了,但是它早已在人们的心中消失了,即便他自己的孩子也不会再想起它。他的孩子并没有受到歧视,改名换姓后和全国其他孩子一视同仁都上了学,现在正为创建更美好的生活而勤奋地学习。然而,总有一天,必须让他们了解他们的父亲因为背叛革命而受到了革命的制裁。他们的父亲是个农民,因疯狂追求荣耀和财富而不惜贪赃堕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不过,他在最后时刻认识了错误,甚至没有一点乞求宽恕的意思,因为他知道自己不配被人民宽恕。让他的子女了解这一点也是公正的。也应该让他们了解,在欧蒂米奥生命终止前的最后时刻,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孩子,请求革命的领导人善待其子女。
此时,一场暴风雨骤然来临,天空顿时阴暗下来。在狂风暴雨中,银色的闪电把漆黑的天幕撕开一道道裂缝,隆隆的雷声滚滚而来,天摇地动。天空刚闪过一道电光,顷刻间一阵闷雷就劈头盖脑地炸响。欧蒂米奥·格拉的罪恶生命就这样结束了,连站在他边上的人也没能听到终结他生命的那一声枪响。
我还记得第二天在埋葬他时的一段小插曲。曼努埃尔·法哈多想在欧蒂米奥的坟上竖一个十字架,但是,我没让他这么做,因为这样会暴露我们处决他的痕迹,会给我们宿营地的主人构成很大危险。所以,曼努埃尔·法哈多就在附近的一个树干上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这就是这个叛徒葬身之地的记号。
“加利西亚人”莫兰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离开我们的。那时他已经知道大家很瞧不起他,我们都认为他将来很可能成为逃兵(有一次,接连两三天不见他的踪影。后来他辩解说他一直在跟踪欧蒂米奥,结果在树林里迷失了)。正当我们准备开拔时,只听一声枪响,结果发现莫兰的一条腿上中了弹。当时在莫兰附近的人后来都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各执一词。有的说莫兰中弹是枪支偶然走火所致;也有人说,是莫兰自己朝自己开了一枪,为的是以后不必再跟随我们队伍了。
莫兰随后的历史——他叛变了革命,最后被关塔那摩的革命者处决——表明他很可能当时在树林里是故意朝自己腿上开枪的。
我们离开时,弗兰克·派斯答应在下个月初,即三月初派遣一批游击队员过来充实我们的队伍,他们将在埃尔希瓦罗附近的埃皮法尼奥·迪亚斯的家中和我们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