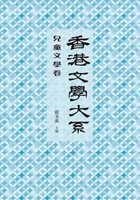
導 言 霍玉英
一
如果說香港「新文學」被視為「小兒科」,(1)那麼,向以為從屬於「新文學」的兒童文學,誠為「小兒科」中的「小兒科」,更不用說她在中國文學廟堂裏能佔一個怎樣的位置。兒童文學既以「兒童」為讀者對象,知識份子中不少因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心心態」,未有想到有了解兒童的必要,更遑論委身「小兒科」,為孩子創作,構築兒童文學的園地。在中國,把兒童看待為獨立的個體,將「兒童文學」看成為認真的事來幹,那要等到周作人高舉「人的發現」後才有所體現。不過,早於一九一二年,周作人在〈家庭教育一論〉裏,已提出中國當下先理治者有二,一曰兒童研究,一曰婦女問題。(2)兒童研究所以前置於婦女問題,那是因為只有明白「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面的生活。兒童期的二十幾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3)不把兒童當作「縮小的成人」,也不輕視他們為「不完全的小人」,讓孩子在尊重中成長,那麼,婦女問題,甚或社會問題、國際問題也許都不再是問題,因為明白彼此都是獨立的個體,有其自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兒童文學中的詩歌與圖畫是幼兒成長中不可或缺,就詩歌而言,周作人在一九一二年〈兒歌之研究〉裏就指出當中道理,「凡兒生半載,聽覺發達,能辨別聲音,聞有韻或有律之音,甚感愉快。」(4)林良從幼兒發展的觀點,把周作人的話演繹得更為寬廣,指出幼兒的第一門文學課程是聽兒歌,幼兒第一門藝術課程是看圖畫。(5)聽歌悅耳,讀圖娛目,一切都如周作人所稱,最上乘的兒童在於「無意思之意思」——「兒童空想正旺盛的時候,能夠得到他們的要求,讓他們愉快地活動,這便是最大的實益,至於其餘觀察記憶,言語練習等好處即使不說也罷。」(6)兒歌兒語並非淺語,她是「淺語的藝術」;兒童文學更非「小兒科」,她是最淺顯,但也最高深的學問。
香港,處於南陲,從地理位置而言,她是「化外之地、邊緣的邊緣」;(7)有學者就政治因素,認為香港「失養於祖國,受虐於異類」,背負無從救贖的「原罪」——殖民統治。(8)不過,以二十至四十年代南來文化人為例,邊緣的香港就提供了特殊的空間,讓他們繼續寫作,不少「在」香港的文學就在這個時期產生,黃繼持稱之為「移入」。(9)李歐梵也指出被政權迫向邊緣化的知識份子縱然流落香港,他們對香港文化和歷史都沒有真正的興趣,因此,在香港掀起蓬勃的文藝活動,只為了向中心喊話,為北返而鋪墊。(10)
三十年代的香港兒童文學,大都依附在報刊副刊而發展,要到了一九四一年才有了第一本的兒童雜誌——《新兒童》。戰後,在香港成立的兒童文學研究組,掀起了華南兒童文學運動,各大報章先後創辦兒童副刊,與一九四六年在港復刊的《新兒童》,以及「叢書」與「文庫」等兒童讀物,進一步推動香港兒童文學的發展。如前述,對南來文人為香港兒童文學的建樹,或許可以有這樣的理解:一、迫於戰爭而避地香港,但在港期間得以繼續創作,既為抗戰大業出力,又可據邊緣小島,向對立政權喊話,宣揚政治思想;二、一九四九年前在港創辦的兒童雜誌與副刊,都成為南來文人的發表陣地,本土的聲音寥落,但又弔詭地培育了讀者和作者,為香港兒童文學埋下種子。
曾經有學者這樣評價四十年代的香港兒童文學:一、創作隊伍並非土生土長,流動性大;二、作品大多來自原作的改編改寫;三、欠缺有生命力的作品;四、兒童文學的評論工作未受到應有的重視。(11)上述批評雖然不無道理,但四十年代香港兒童文學萌發,葉枝並未茂盛,作品生命力或許不足,而改編改寫更不難理解,致使評論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這也是必然的。然而,就創作隊伍的流動性來說,有認為「對香港文學的發展造成了負面的影響」,(12)但也指出是「這個小島城市在文學發展的一個特色。」(13)再證之於政權更替,南北對流,香港又再以她的地理優勢,為右翼文人提供場所,開張另一道風景,並據邊緣小島向中心喊話,此是後話。
如前所述,香港兒童文學向為人所忽視,原始資料缺乏系統的輯錄與整理,更不利尋根溯源,沒法還當年初建面貌。以九十年代出版的「香港文學史」,(14)以及兩種兒童文學史及專著為例,(15)其中雖有專章論及香港兒童文學的發展,但引述大都來自〈華南兒童文學運動及其方向〉一文。(16)一九九六年,周蜜蜜以當事人——作者與讀者的篇什與憶述,輯錄了香港兒童文學的舊日足跡。(17)近年,隨着數碼化的發展,前輩努力輯佚的原始資料得以通達四方,裨益不論遠近的研究者。(18)一九九九年,盧瑋鑾、黃繼持與鄭樹森以國共內戰時間為縱,橫向從原始資料入手,梳理而為三冊資料選及作品選。就兒童文學的範圍,三位學者都有論及,並從報章與叢書篩選具代表性的作品,展現內戰時期此地兒童文學所表現的特色。(19)
過去,由於戰事與政局關係,原始資料散佚不全,就《新兒童》的討論,大都以黃慶雲在一九八○年在《開卷》月刊發表的〈回憶《新兒童》在香港〉為據,(20)沒能讓資料自道身世,誠是可惜。二○○六年,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與香港教育學院圖書館聯合主辦「薪火相傳:香港兒童文學發展六十五年回顧展」,部分在港復刊的《新兒童》(一九四六—一九四九)經數碼化處理後,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資料庫」,研究者於是能據原始資料,尋繹《新兒童》的發展面貌。(21)不過,創刊至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共七十三期《新兒童》,仍湮沒在歷史中。最近,通過「全國報刊索引」,已能檢閱一九四二—一九四九年期間《新兒童》絕大部分的全文,(22)一段空白至今幾得填補,有助還原她的面貌。
二
有謂香港兒童副刊始於《大光報·兒童號》,(23)但就現存資料,僅見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的「兒童號」,眉牌「兒童號」旁註「其弍」。(24)除〈編者話〉及四篇文章外,這一期的「兒童號」刊有一張圖畫(見本卷頁七十),救國主題顯而易見。創刊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的《大眾日報·小朋友》,仍以救國為務,在創刊號署名「大朋友」的〈發刊歌唱〉,即呼籲作為「世界主」的小朋友,「大家同心協力把國救」。(25)同日,署名亦夫的〈小朋友週刊獻詞〉,也期許小朋友能振興救國,以血洗盡世界的污穢,以心在黑暗中放出光明。(26)及至日本大舉侵華,《大公晚報·兒童樂園》亦沿襲救國路線,把寄附在報章的兒童版面,視為一致抗敵的宣傳陣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發表的〈弟弟失學了〉,寫城破軍臨,小孩被迫改用日文課本,讀日本歷史的屈辱,作者在詩首說明中高喊:「救救淪陷區的孩子!」(27)宋因在〈十月天〉,把此地優裕的兒童生活,對比祖國前線士兵的苦寒,呼籲小朋友打破撲滿,捐獻抗戰大業。
一九四一年六月,曾昭森出資創辦《新兒童》半月刊,由在讀研究生黃慶雲出任主編。(28)創辦半年,即因太平洋戰事爆發停刊,離港後輾轉於桂林、廣州及香港復刊。雖然,《新兒童》在港創刊,但在一九四二年桂林復刊首期,曾昭森詳述了《新兒童》在港出版的緣由:
……怎樣去教育這些未來文化的繼承人—兒童—這責任是我們每個年長者所應負起來的。為了這,同人等便組織了進步教育出版社,出版「新兒童」半月刊,想藉一個較易普及而有力的媒介—文字—幫忙我們負擔這重大的使命。為着當時我們工作同人服務和求學的嶺南大學因廣州失陷而遷到香港,我們藉着香港印刷技術及材料的便利,便選擇了香港做出版地,於去年六月一日創刊。(29)
雖然,《新兒童》本無意在香港創辦,但香港的地理優勢、先進的印刷技術及材料的便捷,(30)成就了《新兒童》。情非得已,而在港創辦的《新兒童》,滋養本地兒童讀者的同時,間接培育未來的創作者,那又不啻一段佳話。
《新兒童》創辦人曾昭森,是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一八五九——一九五二)教育理念的追隨者,曾翻譯他的《經驗與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與《我的教育信條》(My Pedagogic Creed)。一九四一年,他以杜威的基本教育理念,寫成〈兒童教育信條〉,三十信條中涵蓋以下三者:一、兒童具有「神聖不得侵犯」的人格,有本身的需要、興趣及要求,此等都應得到尊重,成人與社會應該對兒童的幸福與兒童的人格發展負責;二、兒童教育應以兒童為中心,愛護兒童,全面看待兒童,在生活中顧及兒童的興趣,經驗,能力與需要,而宗教、文學等社會資源亦有助於兒童的發展;三、兒童的發展也具有社會和國家的目的,兒童應該愛自己的祖國,兒童的幸福與兒童的社會教育決定着社會和國家的未來。(31)曾昭森在「附誌」指出,「信條是關於理想的領域,而所謂理想的領域當然不經已成為普遍的認識與現象」,(32)於是,他以此作為進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心思想,而《新兒童》半月刊「就是想把這種見解予以具體的闡述」。(33)
此外,在《新兒童》撰稿的著名教育家,像莊澤宣、唐現之及朱有光等,教育理念雖或不是全然來自杜威,但致力引介西方教育理論和兒童概念,尊重兒童為獨立個體,正是這一批教育家的共同理念。再證之於一九四九年兒童節,以曾昭森為首所發表的〈一九四九年兒童節日兒童文化工作者宣言〉,(34)以及黃慶雲的〈孩權宣言草案〉,(35)莫不呼應着當年的信仰與理想,可見以杜威「兒童為中心」的教育理念,是曾昭森、進步教育出版社及《新兒童》所堅守的理想。
就本卷選收《新兒童》的篇什,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着重兒童心理與趣味。兒童文學的讀者對象為兒童,因此,「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文學反對為走向成人目標而“縮略童年”的功利行為,而是將“浪費時間”的遊玩、閒逛看作是童年期裏正當合理的一種生活態度。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給兒童以擁有自己人生的權利,鼓勵兒童從容不迫地享受童年的幸福,滿足並發展兒童的生命欲求和願望。」(36)四十年代的香港,雖然社會狀況比內地較為安穩,但上述言論也許被視為奢談。不過,審視《新兒童》的作品,也有不少切中兒童心理,着重兒童遊戲精神,能為戰亂中的艱難歲月,帶來一點生趣。呂志澄在〈慕琦的心事〉寫無法接受初生弟弟的慕琦,向父親直抒心中的鬱悶與不平,對讀呂志澄在一九四六年選譯的〈母親的測驗〉,便能明白作者所以確切了解兒童心理,體恤孩子被冷落的心情的原委。(37)再而是〈吳先生和人造雨〉,主人翁吳外錚成功發明人造乾冰以解旱天,但該哪天下雨呢?家中老少各持己見,理由看似合理,但又荒誕滑稽,無疑切合了兒童口味。
黃慶雲在〈鼠寶乘車記〉寫鼠寶誤拉繩子,觸響鈴子,這些連鎖式的情節所製造出來的喜劇效果,也深為兒童喜愛。此外,寓言有所寄託,但往往出於幽默與反諷,像〈王子和魚〉的機智,〈鬥聰明的魚〉的哲思,無不對應了孩子追根究柢的精神。至若賀宜的〈慢伯和他的老婆〉,或意有所指,借以諷喻人生,但仍不失風趣。〈捕虱運動〉的諷刺則較為辛辣,直指當權者的無理與人性的醜陋。在《新兒童》作品中,最為亮眼的是鷗外鷗的〈大衣後面的門〉,弟弟童言無忌,並堅持再三,正表現了兒童的稚拙與想像:
弟弟說:
「這大衣後面的門,
放屁用的罷;
一定是放屁用的門了!」(38)
第二類,培養品德情意。就兒童與遊戲、與玩具的關係,周作人早於一九一四年就有精確的見解,「遊戲者兒童之事業,玩具者其器具」,(39)而「玩具之用,不獨足以娛悅小兒,且可促其智力之發達」。(40)一九二三年,他更斬釘截鐵稱「兒童的文學只是兒童本位的,此外更沒有甚麼標準。」(41)然而,把兒童文學視為伴隨教育而來,承擔教育的功能的論調也有不少。(42)不過,過分強調兒童文學中的教育功用,難免流於教訓,而教條式的告誡,更令孩子生厭。因此,如何堅持以兒童為中心,寓教於樂,則有待作者的拿捏。以珍惜光陰、勤奮好學,做個「新兒童」為主題的作品,就有黃慶雲的〈聽鐘鐘〉、〈春的消息〉、〈不做工的王新新〉。呂志澄在〈聰明的家畜〉以反面的例子勸說遷善改正,雖然曲終奏雅,但運用類近連鎖歌的方式說唱,誠是兒童最喜愛的韻律,一如琅琅上口的遊戲歌。
第三類,從時局出發,向極權控訴、抗戰救國、呼籲和平,以及振興祖國。鷗外鷗在〈尼泊爾王子如是說〉直斥當權者不知民間疾苦,而呂志澄一系列的歌謠,像〈學校門外的李大材〉與〈看看這一羣〉,則反映了迫於生活而為童工、擦鞋童,甚或流浪兒的艱苦歲月。因之,控訴極權,團結或一致抗日,或呼籲停止內戰,建設和平的篇什日多。其中,黃慶雲〈一個真實的敵後故事〉中的新民,〈中國小主人〉裏的小華最為經典,新民和小華不過十歲,但在作家的素描下,他們都成為機智聰明的小戰士,小小年紀或掩護盟軍朋友,逃出淪陷區;或讓父親免於漢奸逮捕,抓住身為父親的偽警隊長鍾大利的心理,最後勸說其加入抗日陣線。這種主題先行的作品,無疑是時代的產物。
抗戰勝利後不久,又掀起內戰,呼籲和平成為這一時期作品常有的題材,像黃慶雲〈為和平而爭〉。〈夜來香〉中的虹之花,因為親睹醫生、護士、築路工人、革命黨人,以及新聞記者不辭勞苦,為改善不滿的現狀而奮鬥,她感動了。最後,虹之花蛻變而為「夜來香」,夜夜安慰着這些為建設美好世界的人。〈詩人〉呢?不再吟風弄月,談愛傷感,作者讓他們到羣眾裏去,並向大眾學習。最後,「虹之花」與「詩人」的追求,在〈兩個小石像〉得見「虹之國」。梳理上述四個作品的發表時序,比較作品的主題演化,也許明白轉變的時局對作者的影響,而早期以改良主義為兒童教育方針的《新兒童》,也日益接近社會,積極宣傳革命思想。
三
就戰後香港文學藝術活動的發展,黃繼持認為「左翼的文藝工作是全國配合的,華南不過其中一個環節。因此,內地多項文學理論及政策趨向往往在香港出現,有部分則加上香港本地色彩。」(43)其中,由文藝協會港粵分會研究部所擬寫的〈關於文藝上的普及問題(討論提綱)〉更開宗明義,指出「普及,是大眾化的具體內容︙︙是我們今後文藝運動的基本路線,同時也是我們作家今後的主要創作方向」,(44)最能表現中共在港粵兩地的文藝政策。沿此,關係兒童文學的發展路向,也不例外。(45)
創刊於一九二一年的《華僑日報》(前身為《香港華商總會報》)是一份工商界出版的報章,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主要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46)總編輯何建章卻能相容左右兩派,予編輯極大自主。戰後,《華僑日報》創辦了不少副刊,其中《兒童周刊》就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創立,(47)主編原來屬意黃慶雲,但她以《新兒童》編務繁忙為理由,推薦學妹許穉人與胡明樹,許為主編,胡則除供稿外,還幫忙編務。許穉人是地下黨員,(48)在《兒童周刊》創刊初期,即以徵文比賽吸納讀者,引領組織「兒童周刊讀者會」,(49)透過多元化的文藝活動培養幹部,積極地回應中共的文藝政策,有鮮明的政治立場。
戰後的香港,經濟尚未恢復,重開或創辦學校並不容易,傳播廣泛的報章於是成為教養場所,並座落於兒童副刊,讓在學與失學兒童,以至生活窘迫的童工都能身受教澤。如果說兒童副刊為教養場所,那麼,「誰來教」的「誰」,就指向主編和作者了,他們不單主導整個版面,又左右了「教甚麼」。因此,許穉人的背景無可避免地影響着《兒童周刊》的編創方向,也就是「教甚麼」的內容。在〈發刊詞〉中,許穉人一方面指出戰後香港缺乏健康的兒童讀物,一方面則呼籲關心兒童的朋友來為這片荒蕪的園地播種耕作,肩負「導師」的重任,引領並鼓勵讀者參與園地的播種與耕耘。(50)
在作品中,許穉人所關注與反映的兒童可分為兩類:一、受壓迫的童工,以〈小倔強〉為代表,在被澤教化之後,他長了知識,添了勇氣,並奮起反抗,在偌大的世界裏尋找自己的路;二、「思想進步」的新兒童,以〈雙十節〉中的小穎為典型,她用「繼承先列遺志,爭取民主、自由」的口號,領導小同學巡遊去。(51)許穉人更喜於作品中說理,在戲劇〈互助〉便借工人葉強的話,指出小乞丐小牛和洪仔並非敵對的對方,真正的敵人是不合理的社會,是站在人民頭上壓迫他們的人。受壓者要過好日子,不出兩者,一、自力更生;二、團結起來改造不合理的社會。
胡明樹在《兒童周刊》也發表了不少作品,但篇幅所限,部分存目。不過,與其他南來文人不同,胡明樹的作品頗能反映香港的地貌風俗,在詩歌〈香港仔〉,他既描繪本土地貌,像香港仔、大澳、大小丫洲,又寫到香港水上人家的生活。題為〈榕樹爺爺契男〉的故事,不單以李妹仔「契榕樹」反映本地風俗,同時又道出父母雙亡、識字不多的他,如何從行乞、偷搶到自力更生,由中環到西環挨家挨戶派送報紙的生活。此外,胡明樹更不避方言俗語,以至髒話,期以表現社會裏最下層、失教報童的語言,又隱隱然指出社會上嚴重的失學失教問題。
《星島日報》兒童副刊《兒童樂園》創刊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晚於《兒童周刊》一年多,主事者如何與佔全港銷量第一位的《華僑日報》爭雄?(52)盧瑋鑾就曾以「高度分工」來形容《星島日報》在戰後創刊的幾個副刊,(53)並歸納對這些副刊的印象。(54)《兒童樂園》在創刊之初,並沒有主編的署名,到第四期改為周刊後,即以「豐子愷題」或「子愷題」的書畫為報頭,主編署名「豐子愷」,直到一九四九年年底。(55)且勿論豐子愷曾否主編《兒童樂園》,但報刊主事者以「兒童的崇拜者」(56)為「主編」,其實反映了副刊的宗旨—「兒童本位」。再而以豐子愷的畫作為報頭,如盧瑋鑾所言,此舉能「建立讀者對編者的信任」。(57)
綜觀在《兒童樂園》所發表的作品,大都以「兒童本位」為宗,着重兒童的遊戲情味,在寓教於樂之餘,又啟發兒童心智。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間,豐子愷在《兒童樂園》發表的作品,以漫畫為主,其中四幅一組的連環畫更是少有。(58)這些作品都「從兒童視角切入,強調兒童的遊戲性,既貼近兒童生活,又表現了鮮活的兒童情趣」,(59)比「人生漫畫」有較多「天真的幻想、對世間濃厚的愛」。(60)〈爸爸吃蛋糕〉與〈西瓜藝術〉兩者都關乎「吃」,前者表現更多的是孩子氣,在聰穎中流露稚拙,在稚拙中又透出聰穎;後者把握了「採」、「吃」及「刻」的「遊戲」,從兒童角度,寫孩子生活中的趣味與遊戲。此外,兩個作品都蘊含「愛」,前者幽默諧謔,後者以「看」,透現了一家四口並坐觀賞西瓜燈的「團圓」。此外,豐子愷以層疊推進的手法寫成的〈為了要光明〉,(61)趣味盎然,他既抓住兒童文學中的遊戲精神,又以幽默有趣的情節表現。唐權的〈縣太爺的公道〉和平浦的獨幕劇〈蒸籠〉,也同以層疊推進的手法,為兒童讀者帶來幽默與諧趣。
此外,發表在《兒童樂園》的篇什少有論說,作者大多採用寓教於樂的方式,通過生活故事寄寓道理。胡叔異以「你不能去了」為題,讓不愛今天的事今天做的文駿,失去與弟妹到海邊避暑的機會。呂伯攸的〈「我們要報仇」〉與嚴大椿的〈老婦的巧智〉兩篇則佈置機關,同以「智取」,前者教訓了愛虐待小動物的小和子,後者則解圍城之困。至於鮑維湘的〈油畫像的故事〉,作者更借助文字遊戲,為兒童提供了一次思辨訓練。
《兒童周刊》與《兒童樂園》兩者,雖屬香港兒童副刊,但意涵不盡相同。首先,套用黃繼持的話,《兒童周刊》誠是「在」香港的兒童副刊,不過,把《兒童樂園》視為一種「出現」的形態,也許較為恰當,因為在「樂園」耕耘的,大都來自上海的作家。其次,《兒童周刊》因編者的政治背景,創刊之初,即不以兒童本位為編寫取向,致使版面表現了強烈的政治傾向;《兒童樂園》則不然,作者與「主編」在兒童文學創作與兒童雜誌編輯都有深厚的經驗,較能遵循以兒童本位為編選與創作的宗旨,為戰後香港兒童提供園地,讓他們在那裏快樂地遊玩閒逛。因此,戰後香港兩家大報的兒童副刊,雖同以「兒童」命名,但表現出很不一樣的風格和面貌,反映了在四十年代末,「南來」——「在」與「出現」在港的文化人,為香港兒童副刊建構的獨異風景。
四
四十年代創刊的兒童副刊,尚有《大公報·兒童園地》與《文匯報·新少年》。《兒童園地》因為寄附在副刊《家庭》,所佔篇幅不多,再因資料不全,能供選輯的作品數量相對地少,其中以詩歌與連環漫畫為主。就詩歌而言,陳伯吹的〈喇·叭·花〉雖然韻律和諧,但以喇叭花喻為「宣傳家」,然後對比「默不出聲」的小草,以及「聽不懂」的桑麻,誠是意有所指。本卷所選麥非發表在《大公報·家庭》的五個作品,都不著一字,單以圖畫講述故事,表現了十足的童趣。其中,〈大人煩惱的時候〉與豐子愷〈我愛人 人愛我〉同以「環形結構」創作,前者講的是煩惱,後者則是愛,是遊戲。
針對較為年長的兒童讀者,《新少年》以「少年」命名,探討議題亦較其他兒童副刊嚴肅,批判意味濃烈。以〈你的爸爸和我的爸爸〉為例,黃慶雲以在上海警司令做事,專抓人的「你的爸爸」,對比了守衛機器和工廠,為解放軍進城做好準備的「我的爸爸」,突顯國共對壘的慘烈,令人悚然。作品刊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這一天,上海解放。其時,內戰雖未完全平息,但大勢已定,左翼文人對新中國的企盼愈演愈烈。加因在〈夢是會實現的〉描繪的是一個令人振奮的「自由中國」,醫院是免費的,學校是集中生活、勞動、娛樂與知識的地方︙︙雖然這不過是主人翁阿麗的夢,但如作品題眼,夢是「會」實現的。加因另一篇作品〈學校的風波〉,以日記形式記錄了學生因反抗學校裏的守舊勢力,連累國文老師,令他被學校辭退,但篇末國文老師的話:「很快的,這種學校,這種不合理的教育會被淘汰的」,(62)也寄託了作者的美好願望。無論是追求夢想的阿麗,抑或反抗守舊勢力的學生,加因在〈四月二十一夜〉予他們莫大的鼓舞與希望——解放軍渡江,受壓迫的人民,受罪的日子快將過去!
戰後,《華商報》在港復刊,她沒有創辦專門的兒童副刊,但偶有兒童文學發表在《熱風》,本卷斟酌收入加因在該刊的兩篇寓言。「將死的狼是最凶殘的,為了更殘暴的報復,狼最善於裝死」,(63)是〈將死的狼〉在篇末的話,當中寓意甚明——提防窮途末路的「狼」。
五
誠如〈華南兒童文學運動及其方向〉一文所言,「本是一個文藝作者的,就應該多懂兒童,多接近兒童,而原來是從事教育的人,就該學習寫作技巧,勇敢嘗試。」(64)這樣,方能融合文藝與教育,使兒童文學能以「兒童本位」出發,配應這一特殊讀者羣的心智發展。不過,成人每每着眼於兒童刊物對兒童所起的教育功效,忽略了這一羣有別於成人的讀者獨有的心理特質與需求。再者,時局動蕩,戰爭不止,成人尚且不能安居樂業,遑論兒童的福祉。在抗戰及內戰時期,香港兒童文學的作者在歷史的漩渦中身不由己地漂流,苦苦探索緊急救國之路、和平之路、擺脫壓迫之路,而「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主張幾成奢談。相對於殘酷的現實,純粹的兒童文學猶如「桃花源」,難免止於作者的理想,而難以實現。
總的來說,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香港兒童文學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創作取向。其一,本着較單純的兒童文學,不牽扯戰爭、壓迫等社會現實,傾向「兒童本位」的創作取向。不過,黃慶雲等在討論華南兒童文學運動的時候,就指出因為時間、環境及許多條件的限制,「發展上自然有許多未達到理想的。」(65)其二,是深受歷史影響,把政治立場和主張加諸兒童文學的形式,甚至主題先行的創作取向,這些作品體現的「成人本位」、「政治本位」,乃是特殊歷史時空的產物。
編輯上述兩種創作取向所形成的文本,有利於梳理香港兒童文學發展的脈絡,從而認清兒童文學的核心|兒童本位。由於歷史與政治的影響,創作偏離兒童本位,誠是遺憾。不過,選編這些作品,能真實反映香港兒童文學的發展情況,顯明香港作為一個邊緣的小島,對華南乃至整個內地兒童文學發展的意義,糾正學界過往對香港兒童文學的誤解與忽視,把她重新呈現在香港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裏,肯定她的價值。
本卷所選作品,大都來自三十至四十年代香港報章的兒童副刊、兒童雜誌、叢書文庫,以及單行本。作品分七類,共一一三篇,包括:一、理論(七篇);二、詩歌(二十八篇);三、童話(二十四篇);四、故事(二十六篇);五、寓言(九篇);六、戲劇(六篇);七、漫畫(十三篇)。以下是本卷所收文本及作者的情況:
甲、香港兒童文學作品主要寄居於報章副刊,而專以兒童為讀者對象的,據所見原始資料,最早僅有一九三三年的《大光報·兒童號》第二期,所刊作品與本卷編選原則相距較遠,不予選收,因此,本卷所選作品起於一九三六年《大眾日報·小朋友》。此外,一九四一年在港創辦的《新兒童》,出版不到半年,即因太平洋戰爭內遷,至一九四六年在香港復刊,後有《華僑日報》、《星島日報》、《文匯報》、《大公報》等報分別創辦兒童副刊或兒童園地,這些報刊資料存世較為完整,因此本卷所選作品以四十年代中後期發表的為多。
乙、《新兒童》從創刊至一九四九年,期間雖因戰事暫停,但仍堅持出版,長達八年。再者,雜誌篇幅較每周不過一版的兒童副刊為長,有較多作品可供編選。因之,《新兒童》的選篇佔最多。
丙、《新兒童》創刊初期,得到不少名家的支持,但仍以黃慶雲的作品為最多,她曾以不同的筆名在《新兒童》發表了大量文章,(66)而呂志澄則在黃慶雲留學美國期間,亦以不同筆名發表作品。黃、呂兩人同兼編者與作者,在頗長的時間裏,支撐着《新兒童》的出版。因之,兩人有較多作品可供編選,所收篇什也較其他作家為多。
丁、就一九四九年前的香港兒童文學,當中有肩負抗戰與解放大業的重任,但切中兒童心理需要,講求趣味與遊戲性的也有不少。本卷在選輯作品的時候,力求兼取兩者,突顯在香港這個文化角力場域裏,有不同兒童概念的展陳,有不同背景影響的創作取向。因此,作品的兒童性、文學表達,以及時代意義都在考慮之列。
戊、本卷收錄了豐子愷與麥非的連環漫畫,收入豐子愷的作品原因有三:第一,在豐子愷的作品裏,四幅一組的連環漫畫是少有的,這些作品不單切中兒童特質,還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其次,豐子愷注意圖像細節,既推動了故事的發展,又起點睛之效,頗具備現代圖畫書(picture book)的雛形。(67)第三,豐子愷四幅一組的連圖只在香港一地發表。麥非的作品以其童真與童趣,別開生面地座落於《大公》,實在難得,本卷亦予以編收。此外,張樂平在《兒童樂園》曾發表十幅以小貓咪咪為主人公的連環畫,幽默有趣,吸引孩子閱讀。不過,因年代久遠,底本模糊,無法修葺,本卷只能割愛。
己、呂志澄有不少發表在《新兒童》的詩作,插圖多由李石祥配製。本卷在編選呂志澄的詩歌時,亦收入這些插圖,讓讀者得見詩歌在《新兒童》發表時的原貌。作者簡介置於呂志澄後。
庚、本卷也從叢書、文庫或單行本選輯作品,其中有許穉人的〈他們的夢想〉。不過,因篇幅所限,如作品在坊間已有出版或再版,則存目以誌,像許地山的《桃金孃》、胡明樹的〈大鉗蟹〉及司馬文森的《上水四童軍》;其他篇幅較長,但不易尋見者,則節錄一二以示,其中有華嘉的《森林裏的故事》。
辛、作者生平可考者,除原居本地外,大都曾在香港居停從事創作;其他只以作品「出現」在香港的兒童版面的作者,本卷亦予選編,這些作者大都來自上海。
壬、本卷只收原創作品,譯作不在選編之列。
六
相對於《香港文學大系》其他各卷,《兒童文學卷》是最年輕的,但知見篇目書目為數不少,惜年代久遠,現存叢書與文庫,難以盡窺全貌,疏漏實在難免。再因選者淺識學疏,在兒童文學領域的研究仍須努力,本卷舛誤與疏漏,誠待有識者指正。在本卷編選期間,得前輩指導教誨,受益匪淺。不過,時光倏忽,因庸怠而錯失機遇,無法再次訪談求教,心中愧疚。此刻,深切體會前輩研究者急於搶救史料的苦心,原始資料與歷史中的當事人是研究的瑰寶,尤其向為人忽略的兒童文學——香港兒童文學。
本卷得鄭愛敏協助整理、校對選文及收集作者資料,另潘爍爍校對文稿,賴宇曼協助後期作品底本訂正,在此並謝。
注釋
(1) 盧瑋鑾〈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漢華文化事業公司,一九八七),頁九。
(2) 周作人〈家庭教育一論〉,周作人著,劉緒源輯箋《周作人論兒童文學》(北京: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二),頁五。
(3) 周作人〈兒童的文學〉,周作人著,劉緒源輯箋《周作人論兒童文學》,頁一二二。
(4) 周作人〈兒歌之研究〉,周作人著,劉緒源輯箋《周作人論兒童文學》,頁四六。
(5) 林良《林良的看圖說話》(台北:國語日報社,一九九七),頁二。
(6) 周作人〈兒童的書〉,周作人著,劉緒源輯箋《周作人論兒童文學》,頁一八六。
(7) 李歐梵〈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初探〉,《今天》,總第二八期(一九九五),頁七六。
(8) 王宏志〈「竄迹粵港,萬非得已」:論香港作家的過客心態〉,黃維樑主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頁七一二—七二八。
(9) 黃繼持〈香港文學主體性的發展〉,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頁九三。
(10) 李歐梵〈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初探〉,頁七七。
(11) 蔣風〈走向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兒童文學〉,《香港文學》第一三七期(一九九六),頁一〇—一九。
(12) 王宏志〈「竄迹粵港,萬非得已」:論香港作家的過客心態〉,頁七一三。
(13) 鄭樹森〈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頁九。
(14) 包括:孫建江《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導論》(南京: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一九九五);蔣風、韓進《中國兒童文學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
(15) 包括: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潘亞暾、汪義生《香港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一九九三);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
(16) 黃慶雲等著〈華南兒童文學運動及其方向〉,頁六一—七〇,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主編《文藝三十年》(香港: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
(17) 周蜜蜜主編《香江兒夢話百年——香港兒童文學探源(二十至五十年代)》(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周蜜蜜主編《香江兒夢話百年——香港兒童文學探源(六十至九十年代)》(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九六)。
(18) 一九九九年,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建立「香港文學資料庫」,是首個系統化的香港文學資料網。
(19) 包括: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九);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上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九);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下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九)。
(20) 黃慶雲〈回憶《新兒童》在香港〉,《開卷》,頁二一——二三,第三卷第一號,一九八〇年六月。同期另有加因(謝加因)〈童話「童話」〉,頁二四—二五。
(21) 出版於二〇一〇年的《大時代裏的小雜誌〈新兒童〉半月刊(一九四一——一九四九)研究》(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一〇),研究者梁科慶所據者,主要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資料庫」數碼版,以及曾昭森編選自《新兒童》一至四八期作品而成的《新兒童叢書》五十冊。
(22) 請參考全國報刊索引網站:http://www.cnbksy.com/shlib_tsdc/article/frontForm.do?articleId=38(檢索日期: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3) 「最早於香港創辦的兒童副刊,是宗教報紙《大光報》的“兒童號”,第一期誕生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周蜜蜜主編《香江兒夢話百年——香港兒童文學探源(二十至五十年代)》,頁四。查現存《大光報》的微型膠卷,缺一九二五年,上述說法有待原始資料的確證。
(24) 老範(潘範菴)的〈編後話〉中有提到「近日兩個專號“黃花”與“兒童”,都是臨時籌備的,一兩日前,才怱怱通知幾位朋友寫稿子……」,文中也指出,「因為稿子多,而且有幾篇是由幾位十六七歲較大的小朋友寫的,我們不便白耗他們的心血,所以再接連出一天」。此外,同版亦刊有「昨天本刊目錄」,四篇文稿分別為:一、老範〈導言〉、碧川〈兒童節談話〉、蘇泉〈可怕的回憶〉及芝清〈一封公開的信〉。由此推測,《大光報.兒童號》應創刊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未能於當天刊出的小朋友稿件,在翌日連出。不過,由於缺乏原始資料,暫無法確證。
(25) 大朋友〈發刊歌唱〉,《大眾日》,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
(26) 亦夫〈小朋友週刊獻詞〉,《大眾日報·小朋友》,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
(27) 徐徐〈弟弟失學了〉,《大公晚報·兒童樂園》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第四版。
(28) 一九四一年的《嶺南大學校報》宣佈《新兒童》的出版:「曾昭森同學發起組織之進步教育出版社,鑒於兒童教育在中國雖已漸形普及,而兒童讀物尚感覺極度缺乏,香港方面小學達一千間,小學生達八萬人,尚未有以純教育為目的之兒童雜誌,特刊行“新兒童”半月刊,以為本港兒童精神食糧之供應。第一卷第一期於本年六月一日出版,執筆者有朱有光,簡又文,黃慶雲等各同學,內容豐富,以後每月逢一日及十六日出版云。」〈曾昭森同學主辦「新兒童」半月刊出版〉,《嶺南大學校報》,第一〇四期(一九四一),第六版。
(29) 曾昭森〈復刊詞〉,《新兒童》,第二卷第一期(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頁二。
(30) 一九二四年,商務印書館在香港設立分廠,及至「一·二八」事件後,更從上海遷來大批技術人員與印刷設備,而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幾經考察,也在一九三四年在香港建立分廠。其後,日本侵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到港,着手擴充分廠,增添機器,並建造倉庫,而陸費逵則在港設立中華書局香港辦事處。於是,香港便成為造貨出版,以及內地轉運,並向海外發展的基地。上述分別見:商務印書館香港辦事處編《商務印書局建館八十周年紀念(一八九七——一九七七)》(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七),頁一〇八。錢炳寰編《中華書局大事紀要(一九一二——一九五四)》(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二),頁一二三——一二四。王余光、吳永貴《中國出版通史·民國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一三一。
(31) 〈兒童教育信條〉在《資治月刊》刊出時,同署曾昭森與黃慶雲之名,曾昭森在附誌指出:「在這信條的草擬當中,黃慶雲同學自始至終也曾給予筆者極大的襄助。她是一位和筆者的兒童教育主張最大相同的一位青年學者。在這裏把這信條發表的時候,筆者和她聯名簽署,是筆者認為極愉快的事情。」曾昭森、黃慶雲〈兒童教育信條〉,《資治月刊》,四卷一期(一九四一年五月),頁一三——一五。其後,〈兒童教育信條〉分別在一九四二年及一九四六年兩度重刊於《新兒童》(第二卷第二期;第十二卷第五期),前者大抵希望內地讀者明白《新兒童》出版社的出版中心思想,後者則或於戰後在香港重申出版理念。
(32) 曾昭森、黃慶雲〈兒童教育信條〉,頁一三。
(33) 曾昭森、黃慶雲〈兒童教育信條〉,頁一三。
(34) 〈一九四九年兒童節日兒童文化工作者宣言〉分別刊於《華僑日報》,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第三張頁四;《大公報》,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第五版;《華商報》,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頁三。本卷收錄的是選自胡明樹《我們的節日》(香港:學生文叢社,一九四九),該書出版於一九四九年四月,聯署人與前述三者略有不同。
(35) 黃慶雲〈孩權宣言草案〉,《華商報.兒童節特刊》,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頁三。
(36) 朱自強《兒童文學的本質》(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一九九七),頁一七。
(37) 〈母親的測驗〉譯自美國的Parents' Magazine,文中提出十道問題以測驗母親的育兒知識,見呂志澄譯〈母親的測驗〉,《新兒童》第十二卷第二期(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頁四四——四六。
(38) 鷗外鷗〈大衣後面的門〉,《新兒童》,第十一卷第五期(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頁七。
(39) 周作人〈玩具研究一〉,周作人著,劉緒源輯箋《周作人論兒童文學》,頁五三。
(40) 周作人〈玩具研究二〉,周作人著,劉緒源輯箋《周作人論兒童文學》,頁五七。
(41) 周作人〈兒童的書〉,周作人著,劉緒源輯箋《周作人論兒童文學》,頁一八六。
(42) 朱自強則在《兒童文學的本質》指出,「兒童文學如果以兒童為本位,它將看到兒童期並非僅僅是為了給成年期作準備才存在,而是同時也為了自身而存在,兒童不是匆匆走向成人目標的趕路者,他們在走向成長的路途上總是要慢騰騰地四處遊玩、閒逛。」朱自強《兒童文學的本質》,頁一七。
(43) 鄭樹森、黃繼持和盧瑋鑾〈國共內戰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三人談〉,載鄭樹森、黃繼持和盧瑋鑾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上冊)》,頁九—一〇。
(44) 文藝協會港粵分會研究部擬〈關於文藝上的普及問題〉,《文藝叢刊》,第二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頁三四。
(45) 有關文藝運動基本路線與《兒童周刊》的基調,請參拙文〈知識的搖籃:香港「兒童週刊讀者會」(一九四七——一九四九)〉,《中國文學學報》,第二期(二〇一一年十二月)頁二九七——二九八。
(46) 〈訪問《華僑日報》社長岑才生先生及編輯甘豐穗先生〉,何杏楓等主編《〈華僑日報〉副刊研究(一九二五.六.五——一九九五.一.十二)資料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華僑日報》副刊研究」計畫,二〇〇六),頁七九。
(47) 在一九四七年春,《華僑日報》除創辦由許穉人主編的《兒童周刊》外,還有陳君葆主編的《學生周刊》,參見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期(下)》,(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頁九三七、九四〇。
(48) 〈訪問《青年生活》編輯何天樵先生〉,何杏楓等主編《〈華僑日報〉副刊研究(一九四七——一九四九)》,頁八八。
(49) 有關「兒童周刊讀者會」的組織與發展,請參拙文〈知識的搖籃:香港「兒童週刊讀者會」(一九四七——一九四九)〉,頁二九五——三一一。
(50) 〈發刊詞〉,《華僑日報.兒童週刊》,第一期(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第二張頁三。
(51) 有關《兒童周刊》作品中所刻劃的兒童形象,可參拙文〈香港《華僑日報.兒童周刊》兒童形象研究(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徐蘭君、安德魯·瓊斯主編《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二三五——二五〇。
(52) 據一九四六年的資料顯示,《華僑日報》銷量為三萬八千份,佔全港第一位。見香港年鑒編輯委員會〈第六篇報社:香港報業史略〉,頁一,《香港年鑒》(香港:香港年鑒社,一九四七)。
(53) 就戰後《星島日報》的副刊,盧瑋鑾談到陳君葆主編的《教育週刊》和《青年講座》、葉靈鳳主編的《香港史地》和《藝苑》、羅香林主編的《文史》、馬思聰主編的《音樂》、焦菊隱主編的《戲劇》,還有張光宇編的《漫畫》和唐英偉編的《木刻與漫畫》,但未提及豐子愷主編的《兒童樂園》、范泉主編的《文藝》和黃堯主編的《漫畫》。盧瑋鑾〈高度分工—略談《星島日報》戰後的幾個副刊〉,星島日報金禧報慶特刊編輯委員會《香港報業五十年—星島日報金禧報慶特刊》,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頁八二、八五。一九九四年,范泉在回復張詠梅信函中提及,他曾主編《星島日報》副刊《文藝》,前後六十期,第六一期是利用他從上海航寄多下來的稿件,再增稿件合成,仍用他「主編」的名義出版。一九四九年初,上海與香港的航班中斷,范泉沒法再航寄稿件。見范泉《范泉晚年書簡》(鄭州: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二一六——二一七。
(54) 盧瑋鑾對《星島日報》戰後創辦的幾個副刊有這樣的看法:一、聘請學有專精的人負責專門版面,組稿有系統、有方針,保持水準;二、編者對主編版面有一定要求,且有較高層次的理想;三、編者都是署名的,讀者完全可掌握和認識編者的品味和個性。盧瑋鑾〈高度分工—略談《星島日報》戰後的幾個副刊〉,頁八五。
(55) 沈頌芳在〈八十風霜—一個老報人的回憶〉中提到,「週刊七種均請名家主編:豐子愷主編兒童,焦菊隱主編戲劇,馬思聰主編音樂,陳君葆主編文史,范泉主編文藝,錢雲清主編婦女,黃堯主編漫畫,並設社會服務專欄,解答讀者來信所提醫藥,法律及日常生活等各種問題。」(沈頌芳〈八十風霜—一個老報人的回憶》,《星島日報.星辰》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第十三版。)雖然,豐子愷曾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至二十三日來港舉辦畫展,其後未有踏足香港。就現有資料顯示,暫難證實豐子愷是否曾經如范泉一樣,在上海「遙控」主編《兒童樂園》。
(56) 豐子愷〈漫畫創作二十年〉,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藝術卷四)(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頁三八九。
(57) 盧瑋鑾〈高度分工:略談《星島日報》戰後的幾個副刊〉,頁八五。
(58) 有關豐子愷在《兒童樂園》發表的四幅一組連環漫畫,可參拙文〈豐子愷「在」香港〉,香港藝術館編製《人間情味:有情世界——豐子愷的藝術》(香港:香港藝術館,二〇一二),頁二八——三一。
(59) 拙文〈豐子愷兒童漫畫與兒童圖畫書〉,方衛平主編《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杭州: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二〇一三),頁一四六。
(60) 明川(盧瑋鑾)〈這是本很特別的畫集〉,莫一點、許征衣編《豐子愷連環漫畫集》,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無頁碼。
(61) 〈為了要光明〉是豐子愷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於杭州所作,曾經配圖三幅,發表於五月十四日《天津民國日報》及八月《兒童故事》第二卷第八期。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文學卷二)(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頁三六九—三七四;盛興軍主編《豐子愷年譜》(青島:青島出版社,二〇〇五),頁四三七。〈為了要光明〉(刊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雖不在香港初刊,但時間相距不遠,推測或是一稿同時分投上海香港兩地。
(62) 加因(謝加因)〈學校的風波〉,《文匯報·新少年》,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第八版。
(63) 加因(謝加因)〈將死的狼〉,《華商報·熱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頁三。
(64) 黃慶雲等〈華南兒童文學運動及其方向〉,頁六八。
(65) 黃慶雲等〈華南兒童文學運動及其方向〉,頁六八。
(66) 在桂林復刊第三期的〈編後語〉,編者介紹當期文稿,當中有杜美譯英國王爾德的〈星孩子〉、慕威續完的〈天鵝哀歌〉、是德的〈地球的故事〉、慶雲的〈聖誕的禮物〉,並稱「本期不是有很多新的作者跟大家寫稿麼?大家都喜歡他們麼?他們都會繼續寫下去呢。」同時,該期還有署名「敏孝」、「宛兒」、「芳菲」、「特行」等人的作品。其實,這些「作者」都是黃慶雲本人,也就是說,復刊第三期幾由黃慶雲一人「包辦」。有關黃慶雲的筆名,可參進步教育出版社同人〈介紹雲姊姊:本刊國內復刊一週年紀念〉,《新兒童》,第六卷第一期(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頁五〇—五一。
(67) 有關豐子愷四幅一組連環漫畫與現代圖畫書的關係,請參拙文〈豐子愷兒童漫畫與兒童圖畫書〉,頁一四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