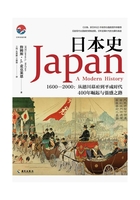
前言
1 966年1 0月一个宜人的秋日早晨,当美国轮船“威尔逊总统”号驶进东京湾时,我从甲板上第一次看到了日本。轮船航行了数小时后抵达横滨。向外望着富士山和草木茂盛、秋果累累的乡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到日本究竟要做什么?那时我刚从密歇根大学毕业,主修的是美国历史,并没有学过有关日本的任何知识,而且我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我之所以到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只是因为一个同班同学对我说,如果我想到他的祖国旅游,他在东京的家人会给我帮助。我是来日本游玩的,但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这次游历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最后使我成为一名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
当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时,我对日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的脑子里确实装了些陈词滥调,比如“日本是个高度一致的社会”,日本的人口属于同一民族;他们看上去很像,想法也相像,而且很容易就任何问题形成全国一致的意见。然而不久,我就认识到这种想法多么不正确。我发现我周围的人们因为年龄、性别、教育和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各成一体。他们对几乎所有事情——例如妇女应该属于家庭还是工作场所,日本应该和美国结盟还是实行中立路线,以及应该称赞大企业为战后国家的富裕做出了贡献,还是应该谴责它们造成了各地的污染,等等。——都表达了迥然相异的看法。我发现,和谐与一致无疑是人们渴望的理想,但实际上,日本人对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看法有很大分歧。
我第一次在日本逗留期间的见闻影响了我对该国历史的看法。如果说激烈的争论和不同的意见在现代日本社会是司空见惯的,那么理所当然,这个国家的历史是其人民在相互冲突的观点之下促使所有事情向前发展的历史。与任何社会中的情形一样,大趋势无疑是很重要的。在此我只列举过去两个世纪里的三个重大肇因: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显然,它们通过影响个体认知自己和世界以及明确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而影响了日本历史的进程。然而,在洪大的历史潮流中,日本人民在他们巨大的多样性中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因此,本书的叙述基于这样的前提,即我们的首要责任是了解不同的个体和社会团体如何明确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然后又如何努力地构建起既符合他们的道德标准和信仰,又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抱负的具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我在与新朋友以及多年的老同事交谈时,还逐渐认识到,大多数日本人比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美国人要更接近他们的过去。也许,这在一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的国度里是很自然的。日本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你可以从容地走出现代地铁,然后躲进古老庙宇的静谧之中,或者坐在咖啡店里,一边享受法式烘焙的咖啡,一边听着最新的爵士音乐,从窗户向外看时,又会发现有身穿传统和服,手提三味线(这种三根琴弦的琵琶在日本近世早期城市中的戏院、妓院等风月场所的“浮世”中处处可见。——译注)的老妇人经过。本书给予日本近世(日本学界常将日本的前近代时期称为“近世”,这是日本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成熟的时期,同时也是孕育着从根本上颠覆封建统治体制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思想意识萌芽的时期。——译注)早期(1 603 ~1 868)的分量反映了日本的现在和过去之间联系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本书还考察了一种允许普通日本人参与乡村和城市自治的政治文化如何促进了近代公民的成长,使公民相信自己有权批评政府的政策,有权组织政治运动和政党。这种政治文化在明治时期(1 868~1 91 2)确立议会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还关注1 8世纪和1 9世纪早期商业的发展和原初工业化如何在1 868年后使迅速工业化成为可能,关于家庭和性别的传统思维方式如何影响到整个现代的行为模式。
我在日本的经历也使我不愿将这个社会或它的历史视为一部成功史。当我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第一次到东京时,触目所及,人民富裕,高楼林立,街道整洁,所有事情都似乎有条不紊,这一切很难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报纸社论和电视纪录片敏锐地指出了日本现代化努力中的缺陷和失败的事实:太多的人依然居住在不合格的住宅里;教育体制强调死记硬背,而不是发展每个学生的天赋与能力;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工作时间太长,以致几乎没有家庭生活的时间。
20世纪后半叶折磨着日本社会的问题,使得甚至像我这样刚接触日本历史的人也很清楚这一点,即不能把日本历史解释为一连串简单的必然通向更加美好和光明的未来的事件。实际上,我的许多日本朋友都不愿说起某些带有历史连续性的让人不快的方面,例如,近世早期对本国下层群体的偏见以及对毗邻的阿伊努人和朝鲜人的轻蔑态度。这样的偏见和轻蔑发展成持续至今的歧视。而且,在过去,当国家处于生死攸关的历史十字路口时,日本人不得不做出使他们的国家和社会走向新方向的決定。如今回想起来,有时他们的选择产生出大多数人都认为有价值的结果,但有时他们选择的道路却导致了几乎每个人都承认的悲剧。我们只需把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和思想的活力与30年代末、40年代初战争期间的压抑气氛相比较,就能发现日本历史有着它自己的残酷的迂回和曲折。
各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尽管存在着某些共性,但却互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相应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当日本人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行事时,只要我们了解形成那些行为模式的价值,它们就不过和其他民族的行为模式一样是可以理解的。换句话说,不寻常和神秘莫测并不是一回事。当我结束第一次日本之行,进入耶鲁大学的研究生院之后,我阅读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一篇文章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ational Theory of Culture”, in h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 Basic Books, 1 973), pp3 -30〕,它帮我把对文化独特性的想法汇集了起来。格尔茨写道,他研究了摩洛哥人,而且对他们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摩洛哥人既合乎情理又富有独特性。他得出结论:“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其常态。”
在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工作时,上述汇集起来的想法为我提供了一系列指导:摒弃陈见,尝试理解激励日本人去行动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正确评价过去的遗产,同时时刻不忘,历史会不断迫使人们做出決定,使他们的未来走向全新的方向;重视那些经历了历史波折的人们的判断,借此评价过去行为的后果;时刻牢记没有唯一的行为模式,其他民族可以从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方式中得到满足,找到生活中的价值。
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并不容易,当格尔茨引用一个英国人的故事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人告诉这个英国人,世界是在一个平台上,平台放在大象的背上,大象站在海龟的背上,然后,这个英国人就问:“那么那头海龟站在什么上面?”他的印度朋友回答说:“另一头海龟。”“又一头海龟?”“哦,从那以后一直在下面的就是海龟。” (印度教认为地球由四只大象支撑,而大象站在海龟的背上。——译注)与此相似,我们可能永远不能看透日本历史的所有深层的东西,我也很少像我所想的那样完全理解某件事情。不过,格尔茨有另外一个想法可以安慰我们大家,即没有必要“为了理解某事而了解所有的事”。在我对日本的研究上,我用这句话来表达这样的意思,即在最深层的本质上,研究历史是一种艺术:猜测人们的动机,评价他们行为的意义,估量我们的观察,然后从我们更深的洞察中得出结论。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对于入门者还是有经验的学者而言,探索日本历史并且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都是很值得的。
詹姆斯·L.麦克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