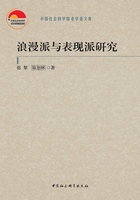
二 “对立论”难以自圆其说
关于启蒙运动与浪漫派的关系,有两种说法流传颇广,一种说法声称: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和理性至上的大旗,而浪漫派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唱非理性、主观主义和感情用事的赞歌。另一种说法宣称,启蒙运动者向前看,世界观先进,而浪漫派则向后看,迷恋中世纪,世界观落后甚至反动。其实,两种说法都是传统的“对立论”的变种,都是站不住脚的。
的确,浪漫派以重主观、厚情感、崇尚幻想著称于世,但他们并不轻视理性,更不会敌视它。1795年,在拜读了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哲学家孔多塞的《论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1795)后,年轻的弗·施莱格尔马上撰文称赞道:“(孔多塞的)论著由于简朴、明快和高贵的写作方法,由于对真理和见识的真诚热情,由于对美德的纯情和由于对偏见、虚伪、压迫和迷信的高尚仇恨而给世人留下美好的印象。”[12]翌年,诺瓦利斯在日记里写道:“务必竭尽全力训练并经常发展和提高想象力,如同理智、判断力等一样。现在我增强理智,就最值得,因为它教我们找到道路。”[13]这些话均出自浪漫派作家之口。18世纪被称为理性主义时代,浪漫派作家在世纪末年的这些表述,均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可见他们并不反对理性,并不反对理性原则。但他们反对理性主义,反对把理性绝对化、教条主义化,反对主观客观的分离和精神与物质的二重性。如果说在18世纪理性主义时代,理性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智与幻想属于一种主从关系,那么在18世纪末开启的浪漫主义时代,理智与幻想固然存在对立的一面,但两者也不相互排斥。奥·威·施莱格尔在一次讲课中谈到两者关系时这样说:“它们仿佛永远对立,因为理智绝对强求统一,幻想则在无限多样性中开展其活动,但它们都是我们本质的、不同的基本力量。”[14]诺瓦利斯对两者的关系的认识是有变化的。在1791年10月5日致赖因霍尔德的信里,他仍把“我的理智大大的占了感情和幻想的上风”看作优点,但是数年之后,在1799年的《断片》里,他却将理智与幻想视为平起平坐的兄弟姐妹关系:“清醒的头脑同热烈的幻想结成兄弟姐妹关系,乃是真正的有利于健康的精神食物。”[15]
尽人皆知,浪漫派迷恋中世纪文化,他们提出了“回到中世纪去”的口号。过去,人们对此不大理解,甚至横加指责,声称这个口号有着反动的含义,认为他们是要回到中世纪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统治中去,“要在新世纪恢复中世纪的生活方式”。这种说法显然牵强附会。其实,这个口号并非浪漫派的政治行动纲领,而只是一种文艺主张。它说明浪漫派对民族传统,特别是对中世纪文艺的向往。他们迷恋中世纪文艺,是因为它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语言生动,表达方式自由。尤其在蒙受异族侵略和压迫时期,他们对民族传统和民间文艺的重视,还含有鼓舞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的因素。他们在搜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特别是中世纪民间文学上,所作出的重大努力和贡献,说明了问题的实质。
启蒙运动与浪漫派同中世纪的关系仿佛背道而驰。其实不然。维尔纳·克劳斯教授1962年在莱比锡大学浪漫派问题研讨会上作的那个非常精彩、备受称赞的报告《法国启蒙运动与德国浪漫派》,对此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他探索了启蒙运动和浪漫派双方同中世纪的关系,根据西班牙启蒙主义学者,特别是法国启蒙主义者如布兰维里埃(Henri de comte de Boulainvilliers)、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Sieur de Fontenelle)、麦西安神甫(Abbè Massieu)和拉加尔纳·德·贝拉叶(Lacurne de Sainte-Palaye)等同中世纪的关系上证实,浪漫派对中世纪的浓厚兴趣,遵循了启蒙运动的传统,植根于启蒙运动的世界观。他们对中世纪的向往,是以启蒙主义者为榜样的。这位教授同时也指出,对中世纪的兴趣产生了有利于反动派的变化,那是在1815年封建复辟之后:“当一个世界性的封建主义大君主政体的卡特尔通过神圣同盟而组成的时候,而且是在一种要确保各民族和平的和平主义的决定性影响下,中世纪意识形态才出现功能的转变。”[16]
从上文不难看出,“对立论”及其变种,都缺乏科学的辩证的分析,远远偏离了客观实际和真理,都是一种偏见,难以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