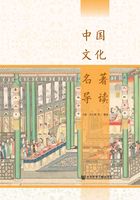
绪论:关于青年必读书
中国文化名著是经数千年岁月淘洗出来的一批记录中国人内在心智和德性的书。它们承载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是理解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入门锁钥。
中国文化名著应该包括哪些书?这是我们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尤其到了大学,要有自己的判断,知道老师推荐书目的标准是什么,这些标准有没有道理。即使认同老师的标准,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也要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保留,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又所谓“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郑板桥诗),努力寻出自己的一条读书之路。
其实,早在百年以前,国内一批大师级学者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影响深远的问题。他们凭借自己深厚的学养、博通的见识以及寄望后学的真诚恻怛,探讨如何为大学青年的国学知识配餐。以下,将带领读者走进“五四”以来多位有代表性的大师名家开列过的经典书目。
一九二三年,胡适曾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一百九十种。后经反复斟酌,又修订精简成《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这个书目,经史子集、辞典佛经、小说戏曲,看似无所不包,却遭到高文博学、著作等身的梁启超的质疑:“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见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考虑到梁任公的学术地位和一流眼光,有必要将他有关的重要议论摘引,以供读者借鉴:
胡君说:“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着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依我看,这个书目,为“国学已略有根柢而知识绝无系统”的人说法,或者还有一部分适用。……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什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还有一层,胡君忘却学生若没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试问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源》,懂他说的什么?
该书单最令人诧异之处是,一份名为“国学”的书单里,有《三侠五义》和《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显然博而寡要,无怪乎梁启超认为是不可用的。梁启超这篇批评一针见血,很有分量,尤其展现出与晚清经学传统截然异趣的史学视野。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具有时代新眼光的白话文和戏曲价值的关注。比如“五四”以来确立的“四大名著”等一批新经典,在正统学人眼中难登大雅之堂,但从结合实际的角度来看,却能跳出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与思想一般不能超出孔孟老庄、诸子百家的狭隘局面。
继胡适之后,梁启超也写出一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里面的书目并非笼统开列,而是有核心、有重点,由内而外依次展现中国文化内涵的一批传统优秀经典。它共分五类: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如《论语》《孟子》)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如《史记》《资治通鉴》)
(丙)韵文书类(如《诗经》《李太白集》《杜工部集》)
(丁)小学书及文法类书(如《说文解字》)
(戊)随意涉览书类(如《徐霞客游记》)
在这五类重要度依次递减的书目基础上,梁氏又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目”,并说:
右所列五项,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1]
或许有读者对最后一句话产生怀疑,觉得梁启超所开最低限度的书目都是传统经史文学类书籍,在学科专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今天,完全不适用。殊不知,钱学森先生就曾明确指出:“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2]抗日战争时期的“兵工之父”俞大维也表达过文理兼通的意思,他说:“我平生得益的只有一部半书。半部《论语》教我处世做人的道理。一部《几何原理》给我敏锐的逻辑思考和高度的判断能力。”[3]
钱穆先生对梁启超的书目曾作过一个精当的评价,他说:
梁氏《书目》蕴含的重要精神,是在脱去教人做一专家的窠臼,不论是经学家、文学家、收藏家或博雅的读书人,以及正统的理学家,梁氏都不在这些方面指点人。梁氏只为一般中国人介绍一批标准有意义有价值的中国书,使从此认识了解中国文化的大义和理想,而可能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社会各方面都有其效益与影响。[4]
钱穆还特别注意到,梁启超的书目精神,很大程度上得自他的老师康有为,即“以孔学、佛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厉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这与乾嘉以来的学者有很大不同,他们只知重经学、文学,提倡“经籍书本”的“博士之学”,到梁氏始转移眼光看重史学。他说“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中最主要部分”。
当然,梁启超的这个书目应与清人袁枚打过的“四部园舍”比喻合观,才能尽得古籍经典的意蕴和妙趣:“‘四子书’如户牖,‘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枢阆,类书如橱柜,说部如庖滔井匿,诸子百家诗文词如书舍花园。厅堂正寝,可以合宾;书舍花园,可以娱神。今之博通经史而不能为诗者,犹之有厅堂大厦,而无园榭之乐也。能吟诗词而不博通经史者,犹之有园榭而无正屋高堂也。是皆不可偏废。”[5]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京报副刊》,刊载了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回应,他的提法比较特别:“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6]作为中国文化名著的推荐理由,鲁迅这段话似宜刊落。但考虑到本教材并非为博雅的读书人选编,而是为文化人格的成就者而选编,以及“世界之中国”(梁启超语)阶段的中国文化名著,必不能自外于世界文化的潮流,所以鲁迅的“不必读”书单实有苦口良药的自省功效。中国古典中的智慧、明哲和超脱,如果没有融入西方的活力、热情和大无畏精神,新的文化气象是无法彰显出来的,而这恰恰是鲁迅反复强调的“行胜于言”的“活人”文化道理。其实,鲁迅本人浸润传统思想文化甚深,也表达过对传统国学的关注。如他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一文中说:
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7]
一九七八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作了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这七部书数量不多,却贵在精要,只是偏重思想文化,哲学味较浓。如能与复旦大学王运熙教授推荐给中文系研究生的书目《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和《汉书》合观,必能打好古文功底,融通文史哲思维,进而在学术殿堂的指路明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指引下,养成人文学术的根基。
在今人推荐的青年必读书中,有几份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一是张岂之先生在《中华人文精神》一书中向大学生和青年朋友推荐的中华文化书目,因为具有哲学思想方面的代表性,所以逐一介绍如下。
(一)《论语》,儒家创始人孔子和其弟子编写的一本书,主要记载了孔子和其弟子的言论。
(二)《墨子》,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全书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其中的《天志》《兼爱》《尚同》《尚贤》诸篇可以细读。
(三)《老子》,也称《道德经》,相传为老聃所著,保留了老子的主要思想。《道德经》有三种,一是通行本,就是王弼注的本子;二是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种;三是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老子》甲乙丙三种。这三种本子当中,最流行的是王弼注的《老子》。
(四)《庄子》,道家又称《南华经》,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著述总集,分《内篇》和《外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周所写,《外篇》以及《杂篇》是其后学所著,共三十三篇。其中的《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知北游》等篇可以细读。
(五)《孟子》,战国中期孟轲及其弟子所著,也有说是孟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的。《孟子》当中的《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告子》《尽心》等几篇都是可以细读的。
(六)《孙子兵法》,共十三篇,春秋晚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其中的《势篇》《虚实》《谋攻》《九变》等篇可以仔细阅读。
(七)《韩非子》,原名《韩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五十五篇。其中的《五蠹》《显学》《解老》篇可以细读。
(八)《荀子》,汉代人称为《孙卿子》,共三十二篇,大部分为战国末期的荀况所著。其中《劝学》《王制》《富国》《天论》《解蔽》《正名》《性恶》诸篇值得细读。
(九)《易传·系辞》,是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著作,约在战国末期成书,又称《十翼》或《易大传》。其中《系辞》上下篇阐述了人们顺应时势、自强不息的道理。
(十)《吕氏春秋》,也称《吕览》,战国末期的秦国宰相吕不韦所著,其实主要是吕不韦召集他的门客所编著,是杂家代表作。其中《重己》《贵生》《爱士》《去宥》《上农》诸篇可细读。
(十一)《史记·太史公自序》,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所著。《自序》主要是司马迁介绍自己的身世以及写《史记》的初衷。
(十二)《论衡》,东汉王充著,其中《自然》《谈天》《实知》《论死》《订鬼》几篇可以细读。
(十三)《不真空论》、《物不迁论》和《神灭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铭文。僧肇的《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是对当时中国佛教所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总结;《神灭论》则是南齐范缜所著,以问答形式阐述“形神相即”的无神论思想,反对佛教形神相异的理论。以上三篇均见于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附录。
(十四)《六祖坛经》,也称《法宝坛经》或《坛经》,是佛教禅宗的代表作,六祖惠能的传教记录。六祖惠能是广东人,禅宗对中国影响非常深远。
(十五)《张载集》,原名《张子全书》,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著作,后由中华书局改版为《张载集》。
(十六)《朱子语类》,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语录汇编。朱熹的《四书集注》影响非常大,《四书集注》也叫《四书章句集注》。
(十七)《传习录》,明代心学家王阳明著。王阳明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和曾国藩都是非常少见的、能文能武的儒生,他的心学著作《传习录》是以问答形式来阐释其心学理论的。
(十八)《明夷待访录》,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的著作,可以仔细阅读其中的《原君》《原臣》《学校》等篇。
(十九)《张子正蒙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著,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思想。
(二十)《严复集》,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著,可以选读其中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天演论·译序》等。
(二十一)《康有为诗文选》,康有为是1898年戊戌变法的倡导者:近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此书分别于1952年和1958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十二)《梁启超哲学论文选》,梁启超是近代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此书198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十三)《仁学》,近代湖南人谭嗣同著,谭嗣同是著名的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该书记述了中国实行变法的必要性及谭氏的哲学、政治思想。
(二十四)《孙中山选集》,民主之父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其中精选了孙中山的著作论文、讲演和函电。可选读其中部分内容。
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推荐的四部经典:《论语》、《老子》、《孙子》和《周易》。这四部书篇幅不大,但代表性很强,有较高的指导意义。按照李先生的说法,“我们的经典,是现代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智慧的四部书。《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讲人文,这两本最有代表性。《孙子》讲行为哲学,《周易》讲自然哲学。讲技术,这两本最有代表性。这四本书年代早,篇幅小,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8]
三是郑丽芬所作的传统经典推荐书目的量化统计。她根据一九九九年北大王余光教授主编的《中国读者理想藏书》中所列的中外推荐书目八十种,又从二〇〇〇年以后出版的中外推荐书目中遴选了八十种,综合出一百六十种被推荐的中国著作书目,排在前十名的是:《论语》(五十八次)、《史记》(五十八次)、《红楼梦》(五十三次)、《庄子》(五十一次)、《诗经》(四十七次)、《老子》(四十六次)、《孟子》(四十四次)、《周易》(三十五次)、《孙子兵法》(三十四次)和《楚辞》(三十三次)。这十部书贯穿了中国从先秦到清代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涵盖了诸子学、文学、史学等诸多领域,至今仍为人们所尊崇。但也有一些经典的影响力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礼记》在二十世纪前被推荐了十八次,二十世纪后却只推荐了两次。另外还有《明夷待访录》《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说文解字》及古典小说等,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影响力有所改变。[9]
四是凤凰网国学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发布的学者赵寻为友人开的教子书目(赵寻:与友人拟《新教子书》)。[10]这份书目包括了中西文经典,其中的中国经典包括四书、经子史、诗文等共计四十八篇(部),分初读参考和进一步阅读书目,也有版本方面的考虑。对于中国之书,赵寻认为应以“四书”为根基——这是中国学问的根本,也是未来中国文明的根本——即以文史为气血,期望能与义理解悟相濡相呴,充实而化成他们的君子言行。而且,在精神上注重对其他文明的汲取,没有任何的自我设限。
然而,这份书单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争论,其中不乏批评、辱骂、嘲笑者,赵寻也被视为“呆子、迂腐、愚蠢”,他所推荐的书读了只能“饿死”,“不如一本《厚黑学》来得实用”。[11]赵寻书目被批评,令人痛心。正如赵寻所言,由于彻底否定文明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存在,一些以吃狼奶长大而自豪的“狼人”们,仍在以各种名义制造黑暗,愚弄民众,致使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积累,却因中西之名、古今之别,不仅得不到深入系统完整的说明,甚至必须反目成仇。为了对治这一中国现代性的顽疾,他才提出了以四书为纲,融合中、西的规划。值得我们深深记取的有这么一段话:“这里要开列的,不是那些要折断他们(即孩子)灵魂翅膀的黑暗与世故之书,也不是那些丢人的按历史教科书排列出的名著大全。它要宽,容得下人类的世代;它要深,映照得出人性的至善。”
通过以上近百年的回顾,我们似乎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读书这件事:书目推荐没有终结,也没有哪一家的“青年必读书”能够完全代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面对体量庞杂的书单,我们或许望而却步,但有一件学林掌故,却足以给人启发:据俞大维回忆,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夏先生对他说:“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年轻的陈寅恪心想:“此老真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但他到七十岁左右的时候却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前引《给陈荔荔的一封信》)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典籍也确实浩如烟海,然而我们不必一一尽览。我们需要做,也可以做到的,就是选取真正的经典文化名著细细咀嚼,好好吸收。
本书从体现中国文化精神面貌的儒释道三教,以及经史子集四部的经典当中遴选出十八部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文化原典,按历史时序和时代影响度对其进行概说和导读,期望能使广大学子得到精神上的涵养与教化。虽然选目不多,但基本涵盖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史类典籍。由于侧重思想类经典,文史名著选入者不多。文史名著仅选入《诗经》《楚辞》《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六部,旨在有限篇幅内凸显文史不分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方便同学们阅读,繁难字标注了拼音,个别字增加了释义。
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既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着重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存在的重要命题。我们以为,倘使中国二千多万大学生对中华五千年的重要文化遗产怀有真正的“温情与敬意”,则以上两个问题便不再是问题,而我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盛况也将足以令人期待、欣喜与叹慰!
[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六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3394页。
[2] 钱学森:《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讲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教书育人》2010年第1期。
[3] 俞大维:《给陈荔荔的一封信》,《团结报》第646期第6版,此据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卞学洛整理,中华书局,2010,第257页。此信亦刊载于台湾1984年1月25日的《中央副刊》,见《李敖大全集》卷28《要把金针度与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第98~99页。
[4] 《钱宾四先生全集》24册《学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第123页。
[5] 袁枚:《随园诗话》卷10,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333页。
[6] 《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2页。
[7] 《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40~143页。
[8] 李零:《我们的经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9] 王余光:《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朝华出版社,2015,第347~348页。
[10] 赵寻:与友人拟《新教子书》,凤凰国学,2015年12月18日,http://guoxue.ifeng.com/a/20151218/46721177_0.shtml;其友旷新年的回应见12月23日网文《学者赵寻开教子书目被批迂腐 清华教授撰文鸣不平》,http://guoxue.ifeng.com/a/20151223/46795161_0.shtml。
[11] 旷新年的回应,《学者赵寻开教子书目被批迂腐 清华教授撰文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