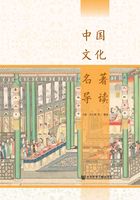
上篇 中国传统思想名著导读
中国传统思想名著概说
中国传统思想名著主要包括儒释道经典和诸子名著。所谓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三教合一,彼此贯通,无一焉而亡,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世界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子书则是六经以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入道见志之书,也就是通常讲的思想家的著作。
儒家的经典汇编是“十三经”,具体包括:一《周易》,二《尚书》,三《诗经》,四《周礼》,五《仪礼》,六《礼记》,七《春秋左传》,八《春秋公羊传》,九《春秋穀梁传》,十《论语》,十一《孝经》,十二《尔雅》,十三《孟子》。它们承载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与价值核心,成为儒家思想的精华荟萃。
“十三经”不是自来有之,而是长期形成的儒家经典汇编,其思想精华最早是“六经”。“六经”并非简单的六本书,而是六位中国先贤认为必不可少的教化方向。“六经”的思想以《礼记·经解》为代表,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1]
王文锦先生的译文作,孔子说:“进入一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教化就可以知晓了。国民们的为人,如果辞气温柔,性情敦厚,那是属于《诗》的教化;如果通达时政,远知古事,那是属于《书》的教化;如果心胸宽广,和易善良,那是属于《乐》的教化;如果安详沉静,推测精微,那是属于《易》的教化;如果谦恭节俭,庄重诚敬,那是属于《礼》的教化;如果善于连属文辞,排比事例,那是属于《春秋》的教化。各种教化节制失宜,掌握不妥,也容易产生各自的偏向。《诗》教的流弊在于愚昧不明,《书》教的流弊在于言过其实,《乐》教的流弊在于奢侈浪费,《易》教的流弊在于迷信害人,《礼》教的流弊在于烦苛琐细,《春秋》教的流弊在于乱加褒贬。为人既能温柔敦厚,又不愚昧不明,那就是深于《诗》教的人了;为人既能通达知远,又不言过其实,那就是深于《书》教的人了;为人既能洁静精微,又不迷信害人,那就是深于《易》教的人了;为人既能恭俭庄敬,又不烦琐苛细,那就是深于《礼》教的人了;为人既能属辞比事,又不乱加褒贬,那就是深于《春秋》教的人了。”[2]
因《乐经》亡佚,汉代只立了“五经博士”,经过汉晋唐宋,才逐渐演变为“十三经”。“十三经”量大浩繁,南宋朱熹删繁就简,编成“四书”,以理学精神加以贯串,虽然简明便学,但毕竟只是“十三经”的阶梯。《四库全书总目》将经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总目》所尊的经乃孔子手定的“五经”,而非朱熹所定的“四书”。真要掌握儒家精义,必然要通“十三经”。为有心志士求学问道计,需要稍微介绍一下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一六年)由江西巡抚阮元主持重刻的宋版《十三经注疏》,其中收录的是历代注释“十三经”的权威版本,具体是《周易正义》十卷,为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二十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唐玄宗注疏的《孝经》石刻版就在今天的西安碑林。还有《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共计四百一十六卷,十一万八千一百页。所谓注和疏都是对经文的解释,疏是在注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可谓解释之解释,所以合成注疏。
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先生对“经”的认识,因为他是站在西学角度下的国学审视,故脱去了传统保守派的迂执狭隘,具有更高的国际视野和比较眼光。
他说:无论你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和《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寅恪先生对玄学的兴趣极淡薄,他甚恶抽象空洞的理论,本人从未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
再讲《春秋》,他除认为《左传》为优美的文学外,对《公羊》“三科九旨”之说很少兴趣。关于《尔雅》,他归于《说文》一类。对《孝经》,他认为是一部好书,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过《礼记》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礼”,认为《周礼》是一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的书,不论其真伪,则不可不研读,他尤其佩服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关于《仪礼》,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虽然随时俗而变更,但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他常提起“礼教”思想在《唐律疏议》中的地位,说这些是人人应该重视的。他认为《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包含了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釆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书,且须要背诵。
次讲《四书》。他说,《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的、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大哲学家黑格尔看了《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后,误认是一部很普通的书,尚不如西塞罗(Cicero)的《论义务》(De officiis)。寅恪先生喜欢《孟子》一书,但对孟子提到的典章制度部分及有关历史的议论,他认为多不可靠。我们这代普通的念书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寅恪先生则不然,他不仅能背诵“十三经”的大部分内容,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3]
道家是儒家之外影响最大的学派。“《易》衍儒、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与儒家相反相成,互补为用,堪称双璧。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给许寿裳的信),英国李约瑟博士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4]对于“根柢”二字,我想可以从现实和超越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现实方面,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道家原本出自史官,对成败、存亡、祸福及古今之道看得比一般人透彻,但又不像太史公那样客观呈现史事真相,而是通过哲学抽象的方式,总结一套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形而上理论,即“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君人南面之术”。按《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说明道家在政治致用当中所体现的致虚守静、有利万物而不争的自然无为特征。超越方面,道家以“道”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和终极关怀,用“道”来统摄自然、社会和人生,全面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满了辩证智慧的光芒。
道家与道教不同,前者是一种思想文化流派,后者是一种宗教,本书侧重于前者。在道家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经典。道家学说的源祖是黄帝,其思想流传至战国,形成《黄帝内经》和《黄老帛书》。《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地相应”(《灵枢·邪客》),人须顺应阴阳才能愈疾保生,阐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法则思想,使它不仅成为最古老的医学经典,也成为重要的道家经典。《黄老帛书》盛行于汉初,本是贵族子弟的必读书籍,但后来失传。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道德经》乙本卷前的《法经》、《十六经》、《称》及《道原》四篇,引起巨大轰动。再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庄周的《庄子》,以及与《老》《庄》并称的贵虚尚玄的《列子》。《列子》一书的真伪至今无定论,但里面几个寓言故事——“愚公移山”、“夸父逐日”和“杞人忧天”,却脍炙人口,引人深思。与道教相关的两部经典,一为西汉蜀地严遵的《老子指归》,该书会通易老,创立了对后代道家易玄人士影响极大的以无为本、无中生有和万物自化的思想体系。二为东汉成书的《老子河上公章句》(河上公为战国时人),作者极为重视养生,并将养生等同于经世治国,身国一理。其中谈到的行气、固精和和养神三术,上承汉代黄老道家之学,下启魏晋神仙道教,为后世道教徒所重视。
佛教是世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由印度的释迦牟尼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创立,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有生皆苦”,提出苦集灭道“四圣谛”,其中的灭苦之理想境界是超脱生死的涅槃。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宣播扩散,至晋以后盛行中土,对我国的文学、艺术、哲学以及社会风俗习惯都有较深影响。自此以降,中国文化就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道、佛三家汇合的文化形态。佛教中国化后形成禅宗,对中国本土文化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典籍浩瀚,有所谓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佛典有经律论、大小乘之分,每部佛经又有节译、别译等多种版本。出于“阅藏知津”的考虑,杨仁山、梅吉庆以及中国佛学院都做过与儒学“十三经”相拟配的“佛教十三经”的选编本,其中最著者包括《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圆觉经》、《梵网经》、《坛经》、《楞严经》、《解深密经》、《维摩诘经》、《楞伽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和《四十二章经》。
印度早期的佛经以上座部的小乘经典为主,经中主要阐明人生无常的佛教基本教义和远离诸欲、弃恶修善、注重心证等修证义理。后来大乘佛教发展,又因其思想内容的不同而分为空、有二宗,空宗的般若浓缩本经典就是《金刚经》和《心经》,其渊海为唐僧玄奘所译之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般若空宗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条件的产物,这个条件就是“缘”,条件具备了,事物就产生(缘起)了;条件消失了,事物就消亡(缘灭)了。除此之外,世间万物都是一成不变、念念不住的过程,因此都是没有自性的,这就是所谓的“缘起有,自性空”,简称为“缘起性空”。有宗也认为外境非有,但又提倡“万法唯识”,即认为一切外法和外境都是“内识”的变现。与印度佛教不同,中国佛教的主流不在纯粹的空、有二宗,而在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心性学说)汇集交融的真如妙有思想。《法华经》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是因为被妄念和情欲遮蔽住了(《圆觉经》),才在六道中轮回,如能即心顿悟成佛(《坛经》),了悟“心净即佛土净”的道理,就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获得《楞严经》所说的“菩提妙明元心”。
赵朴初先生曾说:“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要搞中国古代文史哲艺术等的研究,不搞清它们与佛教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5]可见佛教之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代表性的诸子名著可见《二十二子集注》、《诸子集成》和《新编诸子集成》。诸子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前有老子、孔子及七十子之徒,后有墨、杨、孟、庄、荀、韩之流,是各家为救时急而创立的,习惯上称为诸子百家。汉代司马谈将其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纵横、杂、农、小说四家。《隋书·经籍志》把兵书、天文、历数、五行、医方之类并归子部。《四库全书总目》则确立了子部“三教”“九流”的子学主体。子书是六经流裔,是应时而变的治世理乱之书。因此不同时期的思想实践就体现了不同的精神价值和治世方略。秦为法家思想统治时期,汉初道家黄老无为思想占据主导,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但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魏晋南北朝,道家玄学和佛学思想大放光芒。宋明为儒家理学思潮时代,近代以降中西交会、西学东渐成为新的洪趋。二十世纪是革命与改革相互交织的岁月,疾风骤雨和如油春雨的灌溉让中国步入“富而后教”的春风化雨时代,是全新的文化变奏。
[1]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下《经解第二十六》,中华书局,2001,第727页。
[2]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下《经解第二十六》,中华书局,2001,第727~728页。
[3] 《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台湾里仁书局,1980,第12~16页。
[4] “中国人的特性中,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英〕李约瑟著《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186页。
[5] 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赵朴初文集》(下),华文出版社,2007,第8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