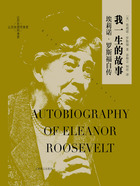
第三章
重返家乡
那年夏天时常有暴风雨。一天,我把普茜给惹恼了。她很直接地对我说,我可能永远不会有家中其他女性那样的追求者,因为我是个丑小鸭。而且,她还说了一些我父亲生命中最后几年的痛苦往事。这样的双重打击令我的情绪极度低落,和我一起在东北港度夏的小亨利·帕里什夫人,想尽办法来安慰我。她竭力想让我快活一点儿,但是在东北港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而且和那里的年轻人格格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那时习惯的英国学校生活完全不同。
我想要回到英国的学校,更多地游历欧洲。在许多次恳求和坚持之下,最后我被告知,如果我能找到人陪我一起去就可以。
我去了纽约,在普茜和莫德的帮助下,得到了我第一套手工定制长裙。这是一件深灰色的拖地长裙,我十分喜欢。
我找了一位教堂女执事作为我伦敦之行以及返程的陪伴。回想起来,这是我经历的最可笑和最疯狂的事情之一,因为我的家人直到为我送行时,才第一次见到她。她看上去相当正派,我对此也深信不疑,结果却是还不如我一个人旅行,因为一路上航程十分颠簸,而我在船靠岸的那天才再次看到她。
对于那个年代丘纳德的小型轮船来说,航程颠簸意味着船上的椅子,如果它们都在外面的话,会被绑在栏杆上。桌上放着行李架,假如你试图在船上行走,会感到自己仿佛正在上山或下山。
自从首次旅行之后,我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尽管一直感觉不舒服,我总是待在甲板上,在那儿一坐数个小时,看着地平线起起落落,大多数时候也在那儿用餐。
我和我的女执事住在伦敦一家酒店旗下的大型旅馆里。第二天我去了学校,十分仔细地将返程船票和足够支付酒店账单的钱给了女执事——这位还要我小心照顾却很少看见的同伴。可是,本来应该是她给我悉心陪伴,令我的家人满意,才是她此行的目的。
学校生活一如既往地充满乐趣。看到我回来,苏维德女士很高兴,那一年,学校里又多了一个小表妹,也令我格外开心。道格拉斯·罗宾逊夫妇带来了他们的女儿,名字也叫科琳娜,也把她交给了苏维德女士。她比我年纪小,非常聪颖,很快就赢得了苏维德女士的喜爱与关注。在体育方面她比我厉害许多,在女孩们中树立自己的地位也比我快得多。
科琳娜姑妈和道格拉斯姑父住在伦敦,对我来说是件开心的事,因为如果附近有亲戚能带我们出去的话,我们是可以被允许偶尔在周末外出的,通常是周六下午。我知道我至少可以去伦敦一到两次,看望科琳娜姑妈;包括后来拜伊姑妈来到伦敦,也是这样。
我唯一的遗憾是,在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举行之前,却不得不回国,那个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在伦敦,泰迪伯父也将作为政府的特使参加国王的加冕礼。
1902年的圣诞假期,苏维德女士带我去了罗马。我们住在一间由旧时宫殿改建的私人旅馆里,这里的房间有着高高的天花板,十分高大宽敞。尽管我们欣喜于房间的美貌,却差点儿被冻死,因为用来取暖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便携炉,炉子中间只有零星的几块煤炭在燃烧,发出微弱的红色火光。
古罗马广场我们去了很多次。在冬日的阳光里,苏维德女士坐在一块石头上,将那段历史娓娓道来,身着托加袍穿梭游走在这里的古罗马男人们,尤利乌斯·凯撒被暗杀的地方,恍惚间我们仿佛置身于那段古老的历史之中。我们看到人们双膝跪地,用膝盖爬上“圣阶(1)教堂”,那时的我还是个愚蠢的小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他们感到羞愧呢!
有一天,我们来到蒂沃利,那里有许多美丽的花园,透过花园围篱的小孔,你可以远远地看到罗马城的全貌。
圣彼得大教堂令我感到极为失望,因为我记得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经亲吻过一座巨大雕像的脚趾。实际上,当时是保姆把我举上去,我才得以完成这个虔诚的动作;但是当我再度回来,看到这尊雕像是如此之小,我甚至不得不深深地弯下腰才能吻到它的脚趾。
复活节到来的时候,苏维德女士再次邀请我与她同游。这一次我们穿越海峡,去她朋友里博的家,在离加来不远的地方。他们住的房子要通过围墙中的一扇门进去,拉一个长柄铁铃铛,就会响起欢快的叮当声传到屋里。几分钟后,我们走进一座开阔舒适的花园,四周绕着一人多高的围墙,给人一种完全私密的感觉,这是法国人十分看重的,即便在城市里的住宅也是如此。
我已经记不起这个小镇的名字了,但是我还记得曾经独自一人远足,想要看看那些教堂以及还能发现些什么。对两位气质高贵而又十分和蔼的主人,我心怀几分敬畏。后来,我在一位法国总理那里又遇到了这次访问的主人。
从那儿我们去了比利时,拜访了苏维德女士的几位朋友,搭乘他们的车做了一次长途旅行。然后我们沿着莱茵河去了法兰克福。
随着夏季的来临,我知道我必须回家,不再回来了。苏维德女士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我最在乎的人之一,一想到要和她长久分离,就令人难以忍受。如果能够再接受一年时间的教育,我愿意不惜代价,然而对于我的外祖母来说,十八岁是女孩子“走出去”踏入社交圈的时间,“不出去”是难以想象的。
当我离开的时候,我笃定地以为我很快就会回来,但是如今我才意识到,苏维德女士心里明白,由于她的体弱多病,与我再次相见的机会已是渺茫。她写给我的那些情真意切的信件,我仍然珍存着。我们之间日渐深厚的友谊都体现在其中,也可以看出在我父亲故去后的这段时间里,这位品质高尚的人对我产生的巨大影响。
我回到蒂沃里,我外祖母的乡下庄园,在那儿度过了整个夏天。这个夏天并不快乐,因为就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在我小时候十分疼爱我的舅舅瓦利,迅速染上了酗酒的习惯。每次放纵自我后,他总会发誓痛改前非,而我的外祖母也总是深信不疑,但是家里年轻一些的成员都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他让他们的日子变得十分难过。
普茜经常外出。莫德嫁给了拉里·沃特伯里,埃迪成为乔西·扎布里斯基家族的女婿,他逐渐显现出和他哥哥瓦利一样的懦弱。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完全失去自制力的人,由此我开始产生出一种近乎夸张的想法,认为有必要完全压制一个人的所有欲望。
我曾经是个不苟言笑的小姑娘,在英国的生活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不需要承担责任、无忧无虑的感觉,但是当我回到美国的家,生活几乎立刻就凸显出严肃的另一面。而且,在刚回来的第一个夏天,我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成为一个满心欢喜初入社交圈的女孩。
我的外祖母几乎完全切断了与邻居们的联系,而瓦利随便遇到什么人,都会表现出夸夸其谈、自吹自擂的样子,我们真的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除非是知根知底的熟人,否则不会有人被邀请来吃饭或是住上一段时间。
那年秋天,我的小弟弟去上寄宿学校。外祖母和我一起带他去格罗顿。她看起来十分苍老,因此真正照顾这个小弟弟的责任,迅速就从她的手中转交给我。她再也没去学校看过他,而我要每个周末都去探望,就像所有尽职尽责的父母那样。他在那里的六年当中一直如此,就像我后来对自己的儿子们一样。
那年秋天,我搬到了位于西37街的老房子。理论上,外祖母也住在那儿,但实际上她仍然住在蒂沃里,徒劳地想要让瓦利留在那里,尽可能地不让他喝醉。
普茜,我唯一还没有结婚的小姨,和我住在一起。和我孩童时期比起来,她的美貌丝毫未减。她的追求者众多,如同众星捧月,而几次恋爱却总是令她精神崩溃。她像那些初入社交圈的少女一样,周旋于各种社交晚宴和舞会。
当然,对于我的“走出去”,外祖母爱莫能助,但是我的名字还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所有人的宾客名单上。我被邀请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我参加的第一场是一个大型舞会,是我的表亲小亨利·帕里什夫妇带我去的。
我的姨妈,莫蒂默夫人,从巴黎为我买来了衣服,我想象着自己衣着考究的样子,但是却吸引不了任何人的注意。我很高,而且舞跳得也不好。出国以前我熟悉的那些女孩都与我失去了联系,尽管后来我与一些老朋友重拾友谊。走进舞厅,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除了鲍勃·弗格森,自从我出国之后几乎没怎么见过他,还有福布斯·摩根,普茜最热情的仰慕者之一。
我想,我事先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和痛苦,否则绝对不会有勇气去的。鲍勃·弗格森介绍了一些他的朋友给我,但我实在无法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是位受欢迎的社交名媛!
我早早地回了家,从那里脱身令我长舒一口气,也知道了在参加任何聚会或舞会之前,我应该有两名同伴,一位陪同晚餐,一位陪同参加沙龙舞会。那些受欢迎的女孩会受到许多男人的邀请,但她只会接受当时比较喜欢的那个。这些舞伴是先决条件,而你也必须在沙龙舞会上跳好每一种舞姿,你受欢迎的程度是由你带回家的礼物数量来判断的。普茜总是比我多得多!我知道,自己是母亲家族里第一个不是美女的女孩,虽然那时我从未向任何人承认过这一点,但我为此深感羞愧。
后来,莫蒂默夫妇为我在雪莉餐厅,当时最时髦的餐馆,举办了一场大型歌剧晚会和晚宴,之后还有舞会。这场聚会帮我找到了一些感觉,一整晚我都站着,和姨妈一起招待客人,不再有那种焦虑不安的情绪。那年冬天,普茜和我在37街的房子里又举办了几次午宴和晚宴。
我逐渐结识了几个朋友,到后来外出社交也变得没那么可怕;但是在这个冬天,当社交成为我生活中唯一的目标时,几乎令我的精神濒于崩溃。不过,我脑子里还有其他事。在其他人接手之前一直是我在照管房子,因为普茜比她年轻时更加喜怒无常,而她的恋情也变得愈来愈麻烦。她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几天,哭上数个小时,也不吃东西。
瓦利偶尔会一个人来家里,只为一个目的:彻底地放纵一下。普茜应付这种麻烦的能力并不比我强。实际上,我没什么其他重要的事,因此有更多时间来应对这种情况,同时有某种力量和决心支撑着我直面自己的胆怯,对于这个特别的冬天里出现的许多问题,我认为我能够比普茜,这位比我大了差不多十四岁的长辈处理得更好。
不过,那年冬天也有许多令人开心的事。普茜在音乐上颇具天赋,因此认识不少艺术界人士,听她演奏,和她一起去剧院、音乐会和歌剧院都是我喜欢做的事。在纽约过着快乐单身汉生活的鲍勃·弗格森有很多朋友,他介绍我认识了画家贝·埃米特,还有他的其他一些朋友,和鲍勃重拾友谊令我感到很高兴。他认为在我们一起参加完聚会之后,送我回家是他的权利,而这对于我来说则是莫大的解脱,否则我就得让一名女仆等着我——这是外祖母立下的规矩。当我想起独自一人游历欧洲的自由自在时,这个规矩就令我觉得好笑。不过,她对鲍勃护送我是接受的,尽管她不曾听到还有其他人也享有同样的“特权”。
鲍勃带我参加过几次在贝·埃米特画室举办的聚会,使我第一次有机会在非正式的场合中,结识那些在艺术和文学领域有所成就的人。比起每天晚上在正式的社交晚宴和舞会上备受煎熬,这种聚会让我感到舒服多了,但是在那个年纪,由于教育所限,我仍然认为所谓的纽约社交圈是非常重要的,我还不愿意自己被人忽视和冷落。
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偶尔见到正在上大学的堂兄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有他的表弟莱曼·德拉诺,以及他家族里的其他成员和他大学里的一些朋友。我想,他的母亲,詹姆斯·罗斯福夫人(2)一定很同情我。
罗斯福夫人和她1900年去世的丈夫,都很喜欢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父亲,他在开始环游世界时曾经和他们一同乘船。他们是如此喜爱他,以至于他们的孩子富兰克林出生时,请我父亲来做他的教父。
我两岁的时候,曾随父母去过他们在海德公园(3)的家。我婆婆后来告诉我,她还记得那时候我被母亲叫做“奶奶”,嘴里含着手指站在门口,以及富兰克林背着我在婴儿室里转圈的样子。我对富兰克林的第一次记忆,是在一次橘色圣诞聚会上。后来,我从学校回家的那个夏天,在纽约中央车站准备乘火车返回蒂沃里时,在车厢里瞥见了他。他看到我之后,带我去见他母亲,她坐在一辆普尔曼轿车里。此后我再没见过他,直到那年冬天,在我初入社交圈的舞会上,他偶尔会出现,还有我被邀请参加过一次海德公园举行的家庭聚会,其他客人大部分都是他的表亲。
我踏入社交圈的那个夏天,没怎么在蒂沃里待过,在那儿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四处游玩,因为到那时我已经交了许多朋友,而且帕里什夫人对我也是一如既往地关爱有加。到了秋天,当我年满十九岁,外祖母决定不再供养纽约的房子,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普茜和我要住在哪里。拉德洛夫人邀请普茜和她同住,帕里什夫人则为我提供了住处。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成熟了许多,决定不能再把又一年时间花在社交上,特别是当我发现,在休闲娱乐方面,在我表亲的家中并不会比住在37街更轻松。她仍然活在一大堆繁文缛节当中,而守规矩现在可不是我的强项。
苏茜表姐(帕里什夫人的女儿)告诉我,我可以偶尔在一楼的一间小会客室里请客人喝茶,但不能随便请人吃饭。我有自己的女仆,不过所有的事都被安排妥当,以便我能够随时随地外出,而且在为我安排的正式午宴和晚宴上,她也十分周到。
有一件事我依然记忆犹新。我花光了自己的零用钱,而且还有一大堆逾期账单,最后帕里什先生煞费苦心地手把手教我怎样记账。他不让我找外祖母帮我付这些账单,而是教我在一段时间里自己逐步付清。这可能是我上过的唯一一堂理财课,我对此永远心怀感激。
帕里什先生身材高大瘦削,留着胡须,气质高贵,虽然有些墨守成规,但他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
那年冬天,我开始在“少年联盟”(4)工作。这个组织当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玛丽·哈里曼,后来的查尔斯·加里·拉姆齐夫人,是发起人。我们并不是什么俱乐部组织,只是一群渴望为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做些有益贡献的女孩们。我们加入组织时,都同意承担做一些工作,怀特洛·里德夫妇的女儿琼·里德,和我负责为利文斯顿街收容所的孩子们上课。琼弹钢琴,我则教孩子们跳健身操和花样舞蹈。
我记得,我们在下午学校放学时到那儿,等离开时天已黑了。琼经常乘马车往返,而我则搭乘高架列车或第四大道的有轨电车,然后走到对面的包厘街。肮脏不堪的街道上,挤满了异域样貌的人,我的心中满是恐惧,通常都是躲在一个街角等车,胆战心惊地看着从附近小旅馆或破旧宾馆中走出来的人,但孩子们还是令我满心欢喜的。我还记得,当一个小女孩对我说,因为她非常喜欢上课,所以她爸爸邀请我和她一起去她家里,想要送我一些礼物时,从心中油然升腾起的自豪感。后来在我管教自己孩子遇到困难时,这件事始终激励着我!
记得有一次,我的堂兄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时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班学生,过来看我,小姑娘们一个个都表现得十分兴奋。
我想应该就是在这个冬天,我开始对莫德·内森夫人担任主席的消费者联盟产生了兴趣。我很幸运,被安排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太太去制衣厂和百货公司做一些调研工作。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些姑娘们要在柜台后辛苦地站上一整天,即使她们有时间坐下来休息,也没有给她们提供可以坐的地方。我不知道制衣工厂应该有什么样的卫生标准,无论是空气质量还是厕所设施。这是我对于此类公益事业的初次接触,当时还只顾着想象自己能在春天之前了结这些工作,回到乡下度过一个轻松悠闲的夏天!
当我试图总结自己在1903年秋天的成长与收获时,我发现自己是个奇特的混合体,在领略了许多生活中不那么愉快的一面之后,仍然极度天真,不谙世事——这些事似乎并没有让我变得更成熟或少一些天真。
在我还是少女的那个年代,女孩子们所受的礼仪培训,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尽管我认为,我在遵守礼仪方面比我的大多数朋友更为严格,但我相信按照这种方式被教导长大的人可不止我一个。
那个时候,除非某个男孩子主动来追求,否则没有哪个女孩子会对男孩子表现出兴趣或任何好感。在你和一个男孩子有信件往来之前,你一定已经非常了解他了。如今,当我看到这些通信时,不由得哑然失笑。几乎没有人敢直呼我的名字,落款也全都是“您真诚的”,坦白表露感情的行为不仅违反礼仪,并且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除了鲜花、糖果或书籍之外,你不能接受男性的其他礼物。如果接受了一名男性的珠宝,而并没有和他订婚的话,你就会被视作放荡的女人,在我脑海中,甚至从来没有出现过和一个男人订婚之前可以允许他吻你的念头。
尽管我也知道人性有弱点,而且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幽默感,但这都没有让我严苛的理想主义和循规蹈矩有丝毫放松。事情对我来说不是对就是错,那时候我还没什么经验,不知道人类的判断是多么容易出错。
我对生活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希望体验作为一名女性各种可能的经历。我觉得必须抓紧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冲动,渴望投入生活的洪流之中,因此在1903年的秋天,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我的第五代远房堂兄(5)向我求婚时,尽管我当时只有十九岁,却认为这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两个都太年轻,还缺乏经验。从格罗顿过完周末回来之后,我问苏茜表姐是否认为我足够认真,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外祖母时,她问我是否确定自己真的在恋爱。我庄重地回答“是的”,然而我现在知道,直到多年以后,我才会明白什么是爱,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我对作为妻子和母亲有着很高的标准,却对成为妻子或母亲意味着什么一点儿概念都没有,我的长辈中也没有人教导过我。现在我很惊讶于丈夫当年的耐心,因为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以前我在许多方面的表现都很勉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早年婚姻生活中的一些糗事是多么可笑。
我婆婆充分认识到我们两个都太年轻和不成熟,她决定劝说她的儿子慎重考虑这件事情——当然,那时候我对此很生气。那年冬天,当他在学业上取得骄人成绩之后,她带着他和他的朋友兼室友,拉斯罗普·布朗,坐游轮去西印度群岛游玩,而我当时还住在纽约的帕里什夫人家里。
不过,富兰克林并未改变心意。
我第一次体验到有总统这样的大人物出席某种家庭聚会,比如婚礼或葬礼时的纷杂场面,是在我的姨祖父詹姆斯·金·格雷西的葬礼上,他于1903年11月22日去世,他的妻子是我们亲爱的格雷西姨祖母,泰迪伯父来纽约参加了他的葬礼。
街上到处都是警察,泰迪伯父所住的道格拉斯·罗宾逊夫人宅邸,只有那些有身份证件的人才能够出入。我们所有人都是开车去教堂,而泰迪伯父则是从牧师的房子,经过一个连接通道从一扇特殊的门进入教堂,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离开。
不料后来我们却听到一件可怕的事,尽管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还是有一个不知名的男子在通道里拦住了泰迪伯父,并交给他一份请愿书。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或者为什么警察没有发现他。幸运的是,他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他令所有人都感到后怕,因为如果他想要袭击泰迪伯父的话,是能够轻而易举做到的。
1903年到1904年的冬季,我已经搬去康涅狄格州法明顿和她同住的拜伊姑妈,要我和她一起去华盛顿住些日子。这时候我已经有一点点自信了,因此当我遇到那些年轻的外交官,和几位即将在华盛顿社交圈里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时,也是十分的开心。我受邀去白宫住了一晚,但一直以来我都对白宫心怀敬畏,所以还是更喜欢和拜伊姑妈待在一起,感觉更放松一些。她为我把所有事都安排地如此妥帖,以至于我自己什么心都不用操。
我跟随拜伊姑妈一起参加她的各种聚会,虽然这令我紧张地手足无措,但同时也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在这些晚宴、午宴和下午茶中,那些风趣睿智、处事机敏的大人物们令聚会妙趣横生,让我感受到生活中不同寻常的精彩体验。
1904年到1905年那个冬季,最令人激动的事莫过于普茜和小威廉·福布斯·摩根的婚礼。2月16日,婚礼在普茜借住的拉德洛夫人宅邸举行。普茜看上去很美,但是没有一个人感到开心。福布斯比普茜小了好几岁,而且我们都深知普茜喜怒无常的性子,禁不住好奇他们两人要如何各自调整,来面对婚姻生活中的琐碎繁杂。
泰迪伯父的总统竞选与连任,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关注,因为我重新回到了那个与政治绝缘的世界。不过,在华盛顿的日子里,我对政治逐渐有了一点儿概念,这是一个与我在纽约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同时,在社交方面我也渐渐地找到了那种轻松的感觉,这是我迫切需要的。
泰迪伯父偶尔会私下来拜伊姑妈的住所,他的到访是令人开心的事情。拜伊姑妈时常会和伊迪丝伯母一起散步,泰迪伯父有时也会派人请她去讨论些事儿,以显示对她意见的重视。他对自己的两个姐妹都很关心,科琳娜姑妈(道格拉斯·罗宾逊夫人)会来看他,他也会去纽约或乡下看望她。他们会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以及文学或艺术,他的妻子和姐妹们,都会各抒己见,谈话总是热烈有趣,兴致盎然。
拜伊姑妈在家居料理方面很有天赋。即便是一些丑陋不堪的家具,她也能营造出一种舒适温馨的氛围来。她的谈吐生动有趣,而她的热情好客总是令人如沐春风。不速之客也能受到热情款待,无论老幼,你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拜伊姑妈对你的关心。
那时的我仍然十分腼腆羞涩,而她一直给我以安慰和信心,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和她在一起的原因。她曾经给过我一个建议,一定是出自她自己的生活哲学。我问她如果被别人批评质疑时,怎样才能确定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她的回答是:“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有人质疑你,如果对于那些你爱的和爱你的人来说,你确定自己问心无愧,并且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那么你就不需要担心那些批评质疑,也不需要做出解释。”
她自己多年来就在践行这一原则。J.R.“罗西”·罗斯福(6)在伦敦担任使馆第一秘书的时候,妻子去世了,她承担起女主人的职责,照顾他的孩子们。在那儿她遇到并嫁给了使馆的海军武官,威廉·谢菲尔德·考尔斯上校,并在回国后生下了小威廉·谢菲尔德·考尔斯。由于她的残疾和年龄,所有人都为她担心,但是勇气帮她度过了难关,一个健康完美的孩子诞生了,并且母子平安。
拜伊姑妈的丈夫威廉,现在是海军的一名将军,我因此也逐渐开始对军队中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发现我们的这些陆海军军官们,虽然拿着微薄的俸禄,却以能为国效力而深感自豪。他们和家人所拥有的地位,是基于他们的付出而获得的权利,与出身和收入无关。这些对于一个来自纽约的乡下小姑娘来说,是此前从来不曾知晓的!
1904年6月,我和富兰克林的母亲,以及他的众多表亲,去参加他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毕业典礼。那年夏天,我去缅因州的艾尔伯勒看望姑妈道格拉斯·罗宾逊夫人,她在那里有一栋乡间别墅,我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然后去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的坎波贝洛岛,同富兰克林还有他母亲会合。富兰克林来接我,我们乘坐火车,至少换乘了两次,直到傍晚才抵达。当然,我必须带着我的女仆,因为我不能单独和他一起去!
不过,一到了那里,我们就一起散步,驾车环游全岛,和他母亲以及其他朋友乘坐一艘小船出海航行,彼此间比以前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并不习惯奢华生活的我来说,这艘游艇就是奢侈品。
1904年秋季,我们宣布订婚。富兰克林的舅舅和舅妈,沃伦·德拉诺夫妇,邀请我去马萨诸塞州的费尔黑文和整个德拉诺家族一起过感恩节。这对我无疑是一次严峻考验,不过我已经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熟悉了,而且他们是如此的热情亲切,令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家族中的一员——它确实是个大家族。
我婆婆的祖父,老沃伦·德拉诺,曾经是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一位船长。1814年,从瑞典返回的途中,他的船被英国人俘获,他则被带到了哈利法克斯。最后人虽然回了家,船却被夺走。我婆婆的父亲,小沃伦·德拉诺还记得,也是在英美之间的那场“1812年战争”(7)中,费尔黑文被英国人攻占,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他和他年幼的兄弟们被匆忙带到阿库什内河的安全地带。
退休时,德拉诺船长为自己建造了一栋房子,用石块砌墙,有花园和草地,房子的外形不太规则但颇有气势。后面还有个马厩。当他的儿子,我婆婆的父亲小沃伦·德拉诺十七岁时,德拉诺船长把他带到波士顿,让他在朋友福布斯的账房里工作。一个大家庭的长子必须早点学会自食其力,在他还不满十九岁的时候,就成为一艘船上的押运员,远赴南美和中国了。后来他不仅帮助自己的兄弟找到了谋生之路,而且还给予自己的姐妹和其他亲戚许多照顾。
当他和凯瑟琳·莱曼结婚时,生活已经十分富裕,他的岳父母莱曼法官和夫人,是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纽约的拉斐特街区有一栋房子,后来又在纽约哈德孙河边上的纽堡,建造了一栋名为“阿尔戈纳克”的宅子。他在中国住过许多年,是旗昌洋行(8)的创建人之一。
在沃伦·德拉诺船长去世之后,费尔黑文的房子由当时所有居住在里面的兄弟姐妹继承。家族的后人全都是小沃伦·德拉诺的孩子,因为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子嗣。
第三代的沃伦·德拉诺,是我婆婆的长兄,也是我和富兰克林订婚时这个家族的族长。他管理着费尔黑文的财产以及相关的信托基金。家族成员只要愿意可以随时去那儿。
我渐渐喜欢上了丈夫家族中的一些长辈。沃伦·德拉诺夫妇一直对我很好,还有福布斯夫人、希契夫人、普莱斯·科利尔夫人和弗雷迪里克·德拉诺(9)夫妇。
希契夫人是我丈夫家族中最热心公益慈善的。她住在家族在纽堡的老宅子里,她不仅是纽堡公益活动的策划人,还将活动拓展到纽约市,并参加了早期诸多致力于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州和全国性的活动。在我丈夫进入政界后,她对他极为关注,还给他写了数封关于地方政治形势的长信。
弗雷迪里克·德拉诺先生早年还在经商,不过后来当他移居华盛顿后,就全力投入公共事务,成为不只是社团甚至是全国性的领导人物之一,他将过去叱咤商界的能力投入公众事务当中,虽然这些工作没有任何报酬,但是他的努力程度,与之前赚取大量财富的时候并无区别。
我丈夫家族里的所有成员都颇具经商才能,在商业方面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和眼光。这并不是说他们从来不曾犯过错,而是他们整个家族齐心协力,通常能够弥补错误,然后整个家族都会受益。
费尔黑文宽敞的大宅进行过数次扩建,里面有不少新鲜有趣的玩意儿。大门上挂着金羊毛骑士约翰·德·兰诺伊的彩绘勋章盾牌,他是1621年11月家族最早登陆美国的菲利普·德·兰诺伊的祖先。古色古香的家具上放置着陈列架,摆满了各种各样新奇的小装饰品,还有一些精美的中式花瓶。
在阁楼里,摆放着一些象牙雕刻,那是海员们在漫长的捕鲸航程中的作品。现在,这些物件大部分都收藏在新贝德福德博物馆,不过那些装在箱子里的旧时航海日志和家族日记,才是富兰克林尤为钟爱的。
豪尔家族已经许多年没有举行过大型的家族聚会了,可能是由于外祖母和瓦利在蒂沃里的生活并不那么愉快,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分散在各地,并且也没有想要共聚的兴趣,我们只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个人感情而联系在一起。
因此,第一次参加在费尔黑文举行的这场家族大聚会,令我感触颇深,我感受到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不知不觉间如释重负,因为在过去的那些年,我在豪尔家族的大部分人际关系中都会有某种不安全感。比如,莫德和她那颇有风度的丈夫彼此相爱,但是财政困难却始终如影随形。看上去,他们是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青春佳偶,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他们曾经来过英格兰,因为拉里·沃特伯里(莫德的丈夫)是美国国际锦标赛马球队的队员。莫德的衣着打扮和始终洋溢的快乐令我满怀崇敬与艳羡。他们的世界里充满了欢乐,不过,在这种兴奋和快乐之下,始终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
1902年的时候,我对人们债务缠身的感觉已经开始有所体会,埃迪和瓦利两个人将继承的财产大肆挥霍,普茜怀着美好的愿望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交给别人打理,然而缺乏商业眼光使她亏的比赚的多,因此到那个时候,她的收入也大幅减少了。
我的外祖母,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钱也越来越少了,因为没有遗嘱,她只享有亡夫遗产中配偶的份额。她勉强能够支付自己的开销,还要帮助那几个大手大脚的孩子。
蒂茜的丈夫很富有,这些年来蒂茜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家人身上。他们之所以都觉得自己经济拮据,主要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多少有些喜欢与人攀比。
德拉诺家族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想干嘛就干嘛,从来不用为钱发愁的人,而不久我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是我婆婆教会了我,不过我相信她家族中的任何人都有资格教我。在我眼中曾经认为他们挥霍浪费,但实际上他们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他们慷慨大方,能够负担得起大笔开销,是因为他们几乎不会把钱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如果他们中的一个遭遇了不幸,其他人会立刻伸出援手。我们豪尔家族的人也想要团结,但他们却没什么东西能够拿得出手。当然德拉诺家族的人互相之间也会有不同意见,如果是这样,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表达出来。但如果是某个外人,即便只是含沙射影地批评,整个家族也会把他撕成碎片!
富兰克林在进入哈佛之前,就想过要加入海军。他父亲认为,作为家中独子,不应该选择这样一个会让他远离家人的职业。他希望富兰克林学习法律,为日后进入商界或其他行业做准备。
从哈佛毕业后,富兰克林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他母亲在麦迪逊大道200号有一栋房子,1905年的冬天,我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为我们举办的各种聚会,开始陆续收到的结婚礼物,苏茜表姐帮我置办嫁妆和衣服,一切都令人兴奋激动,而婚礼安排由于泰迪伯父——当时的美国总统,将要来纽约为我送嫁而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的婚礼日期必须配合他的行程安排。最后,我们的婚礼确定在1905年3月17日,圣帕特里克节当天,因为泰迪伯父将会参加那天的节日游行。
当富兰克林和我受邀与拜伊姑妈一起参加1905年3月4日举行的泰迪伯父的总统就职典礼时,都激动万分。在国会大厦,只有直系亲属才能入内。我和富兰克林的座位就在泰迪伯父和他家人的后面。我十分地兴奋好奇,不过那时候我对于政治仍然一窍不通,因此虽然能记得泰迪伯父发表演讲时那铿锵有力的气势,却一点儿想不起来他都说了些什么!我们回到白宫吃午餐,然后观看游行,之后就返回纽约。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经历了一个历史时刻——我从来不曾料想,能够再参加家族里另一位总统的就职典礼!
(1) 圣阶(Holy Stairs),根据罗马天主教传说,圣阶是通往耶路撒冷彼特多斯彼拉多大礼堂的台阶,耶稣基督受难时沿此台阶踏上了审判之路。——译者
(2) 萨拉·安·德拉诺·罗斯福(Sara Ann Delano Roosevelt,1854—1941),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的母亲。1880年,萨拉嫁给了罗斯福总统的父亲老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 I,1828—1900),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译者
(3) 海德公园(Hyde Park),是罗斯福总统的故居,坐落在纽约州哈德孙河岸边。——译者
(4) 国际少年联盟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Junior Leagues International),是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和美国的少年团体的非营利性教育和慈善组织,旨在通过志愿服务来改善社区,并通过培训来提高其成员的公民领导能力。——译者
(5) 第五代远房堂兄(fifth cousin once removed),在英文中用“X cousins Y removed”来表达旁系亲属的远近关系,其中X代表两个隔代旁系亲属中辈分最高的一个离共同的祖先(从祖父开始算)的辈数;Y代表两个旁系亲属之间本身相差的辈数。——译者
(6) 詹姆斯·R.罗斯福(James Roosevelt Roosevelt,1854—1927),昵称“罗西”(Rosy),美国外交官,曾在维也纳和伦敦的外交使领馆任职,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同父异母哥哥,是罗斯福总统的父亲老詹姆斯·罗斯福与第一任妻子丽贝卡·布里恩·霍兰德(Rebecca Brien Howland,1831—1876)的儿子。——译者
(7) 1812年战争(War of 1812),又称第二次独立战争,是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于1812至1815年的战争,是美国独立后第一次对外战争,英国人将其视为对法国拿破仑战争的次要战场。——译者
(8) 旗昌洋行(Russell&Company),是19世纪远东最著名的美资公司,1818年由美国康涅狄格州商人塞缪尔·罗素(Samul Russell,1789—1862)创办于广州,从事广州至波士顿之间的跨国贸易。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小沃伦·德拉诺,1830年起成为旗昌洋行的高级合伙人,带领自己的妻儿包括罗斯福总统的母亲萨拉在香港生活多年。——译者
(9) 弗雷迪里克·德拉诺(Frederic Adrian Delano,1863—1953),曾任美国莫农铁路公司总裁、美国一神教协会副主席和首都公园规划委员会主席,是罗斯福总统母亲萨拉的弟弟。——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