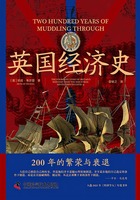
第3章 英国“的起飞”[1]
从全局的全球经济史来看,相比起具体到“英国”,工业革命起源于“欧洲”这个事实更重要。18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是中国和印度,而西欧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总量大概可能与前两者相提并论。在接下来两百年里,世界的经济重心迅速向西移动。到1900年,西欧的经济总量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5%左右,它的分支美国又占15%左右,中国和印度只各占10%左右。这种经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政治影响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全球历史定下了基调:西方的崛起、欧洲的扩张和帝国的时代。仅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业革命前的经济活动模式才开始慢慢地重占上风。
从全球角度来看,“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法国、德国或荷兰?”的问题可能显得微不足道。至关重要的事实是,它开始于欧洲。但从英国历史这个更狭隘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是英国?”这个问题显然更重要。因为英国最先开始工业革命,所以它立即获得了领先优势并保持了数十年;因为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高于人口众多的欧洲其他国家,所以它的经济规模远远大于更大的国家。
1700年,英国和爱尔兰的总人口约为870万,而法国为2140万。到1800年,英国和爱尔兰的总人口已上升到1560万,但与法国的2670万左右的居民相比,仍然相形见绌。但是由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人口与收入的脱钩意味着权力动态发生了改变。1700年,法国的经济规模几乎是英国和爱尔兰的两倍,但到了1800年,尽管法国的人口比英国和爱尔兰多大约60%,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基本持平。与其人口水平相比,英国能够把握住一个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并且在许多方面不止于此的超大的世界角色(以及由它带来的所有优势和劣势)。
英国确实有一些天然的地理优势。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岛屿,英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直接出海,再加上大量容易通航的大河,使得运输和通信成本相对于德国或法国来说比较低。在蒸汽时代之前,在水上运输货物比在陆地上运输要便宜得多。除了较大的河流外,英国还拥有丰富的快速流动的溪流和小溪,这对水磨的运行至关重要。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水力给蒸汽动力让位,英国凭着容易获取的煤层继续为增长提供动力,在能源方面仍然能做到充分的自给自足。对于一个小国来说,英国的地形异常多样化,这使得其不同地区能够发展各种不同的农业。英格兰西北部的潮湿气候可能近几十年以来对支持黑池(Blackpool)的旅游业没有多大作用,但对加工原棉肯定有帮助。所有这些都起到了作用,但“为什么是英国?”这个谜题不能仅通过地理来解答。
正如工业革命塑造了后来的英国历史一样,它本身也是由之前发生的事情所塑造的。从工业革命本身开始时才开始记录工业革命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工业革命的前夕,英国,更确切地说是英格兰,已经是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在工业化的“大分流”之前,曾出现过“小分流”,即欧洲内部财富和经济富裕程度的转移。许多有助于解释工业革命和大分流的因素都可以追溯到其早期的表亲。了解“小分流”,或者说了解英国是如何在19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的,对于理解后来发生的事至关重要。
在公元1000年的第一个千年之交,欧洲最富有的地区——地中海盆地已经维持了1000年。罗马帝国可能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衰落了,但后罗马时期的意大利和摩尔人的西班牙仍然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不过,到1700年,欧洲大陆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地中海的温暖海岸决定性地转移到北海(North Sea)的寒冷地域。就人均收入而言,1700年的经济领袖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荷兰的旧称)和他们在大洋彼岸的商业对手——英国。
经济史学家们已经确定了推动这种分流的两个关键转折点。在经济术语中,这些转折点常被描述为“冲击”(shocks),而其中的第一个就着实令人感到“冲击”:黑死病。
大瘟疫的规模至今仍让人触目惊心:欧亚大陆上的大约7500万到2亿人死于这次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行病。全球人口花了两百年时间才恢复到瘟疫暴发前的高峰。说来也怪,那次瘟疫的暴发本身也许就是由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开始的原始全球化[2]的早期形式的结果。
成吉思汗在1206年统一了蒙古,到他1227年去世时,已经建立了一个占地520万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的帝国。到他的孙子忽必烈(Kublai Khan)去世时,也就是不到70年后的1294年,蒙古帝国的面积已超过900万平方英里,西起今天的匈牙利,东至今天的中国和朝鲜,沿途还囊括了中亚、乌克兰、俄罗斯南部、伊朗和伊拉克。蒙古人征伐之功的关键在于他们有能力调动当时世界上将近一半数量的骑兵,虽然蒙古军队的人数很少超过10万人,但他们的每一个战士都可以获得多达20匹的替换马,这保证了他们在决定性的战斗中总能有生猛的战马和几乎前所未有的灵活性。
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政治统一推动了经济一体化。蒙古人的统治使旧丝绸之路沿途更加安全——只要准备好“买路财”就可以了,在1250年至1350年,这些道路比之前的几个世纪要繁忙得多。马可·波罗可能是这个时代访问过中国的最著名的欧洲人(也可能不是,他的记载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但他远不是唯一的一个。笨重货物的陆路贸易仍然昂贵得令人望而却步,但单位重量价值高的物品——香料、皮草,当然还有丝绸——开始比以前更多地流动起来。思想也不那么笨重了:14世纪的欧洲创新因为中国技术的流入得到了很大的推动。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620年写道,有三项伟大的发明改变了世界: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他很可能不知道这三项发明都起源于中国。
在黑死病之前的那个世纪,人口、货物和思想开始在欧亚大陆上流动。正如罗纳德·芬德利(Ronald Findlay)和凯文·奥罗克(Kevin O'Rourke)在其举足轻重的全球经济史著作[3]中所说:
“全球化”到底始于何时?答案固然取决于具体采用的“全球化”定义,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作出如下有说服力的解答:全球化肇始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当时蒙古人的征服运动统一了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在这些征服运动的冲击下,那些定居文明也相应作出了反应。而在此之前,每一文明虽然也曾意识到其他文明的存在,但只是把它们看作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没有视为一个统一体系中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
货物自由流动,思想、人口畅通往来,但一切还不止于此。欧亚大陆的政治统一推动了经济一体化,这反过来又创造了一位历史学家所谓的“细菌共同市场”(microbian common market)。在中亚某处干燥的平原上,黑死病开始了。商人、士兵和旅行者把它沿着丝绸之路带到克里米亚,在那里它登上了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前往西欧的桨帆船。
在五年的时间里,欧洲有40%~60%的人口死亡。虽然这显然是一场人类灾难,但这也可能是马尔萨斯牧师的“积极抑制”运作的一个光辉典范,即使是像这位好牧师那样具有理性和逻辑头脑的人,在当时也可能很难看到其中的益处。
在14世纪中期具有“马尔萨斯”特征的世界里,一件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没有摧毁建筑物或直接影响牲畜或庄稼的事件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和食物留给了更少的人和胃。人口可能会减少,但人均收入会增加。
面对同样的经济和生物冲击,北海和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英格兰和荷兰,每一个(幸存的)人的收入跃升并保持较高的水平,而在意大利,最初的跃升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就消失了,在西班牙,瘟疫给人们带来了痛苦,却未曾带来一线曙光。
14世纪50年代的西班牙正处于“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阶段,即基督教欧洲“重新”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它基本上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前沿经济体,人口急剧下降的后果是扼杀了商业网络,而不是增加了幸存者的资源。在这里,人口减少并不意味着“为幸存者提供更多的庄稼”,而是意味着“没有足够的人去耕种田地”。在意大利,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人均收入提高后,马尔萨斯的逻辑开始发挥作用,更快的人口增长将收入拖回到灾难前的水平。
相反,在北海地区,黑死病带来的经济成果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两个地区的关键差异在于其农业结构、结婚年龄和生育模式,以及其政治和国家结构。
北海的农业比地中海的农业更注重牧业,也就是说,比起庄稼和植物,更注重动物和牲畜的利用(当然,整个欧洲都有谷物种植)。典型的意大利特色农业产品有橄榄油和葡萄酒;而典型的英国产品有羊毛和羊肉。14世纪50年代,英国农业的经济产出有一半以上来自牛奶、肉类、羊毛、皮革和其他动物制品,而不是直接来自土壤。这种农业通常比耕作需要更多的工序,尽管它产生的人均热量并不高,但比起地中海沿岸的农业种类,它的“经济附加值”更高,或者用更简单的话说,“更有利可图”。
比起耕种农业,这种农业使用的劳动力也更少,用经济语言来说,是更“资本密集”的。“资本”是标准的经济学术语,指除用于生产产出的人(劳动力)以外的任何东西,在此处,“资本”是指牲畜本身。最后,这种以动物为重点的农业在使用非人力能源方面更为广泛——与意大利的农场相比,英国的农场更多地利用马(和牛)力而不是人力。这种高附加值、资本密集、非人力能源密集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仅能更好地应对黑死病后的人口下降,而且还为生产技术提供了模式,这些技术将从农业扩散到工业和(后来)在现代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服务行业。
在中世纪的欧洲,结婚年龄是总体生育率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一般来说,更早结婚的妇女会生育更多的孩子,在地中海地区,女性结婚的年龄比北海地区的女性要小,且往往小很多。1965年,统计学家和人口学家约翰·哈伊纳尔(John Hajnal)提出了他所谓的“西欧婚姻模式”(Western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其特点是男女双方结婚相对较晚且年龄相近,相当数量的女性保持未婚,新婚夫妇通常与各自婚前的家庭分开并建立自己的家庭。除了东南亚的一些地区,这种模式在20世纪末之前几乎是欧洲独有的。即使在欧洲内部,这种模式也不普遍,地中海地区的家庭更有可能由相对年长的男子与更年轻的女子(或在许多情况下是女孩)结婚组成,数世同堂的大家庭是常态。
中世纪典型的英国新娘是20岁出头,嫁给一位大她一两岁的男人,而在意大利,一个21岁的未婚女性会被认为已经错过了最佳适婚年龄。13岁的朱丽叶·凯普莱特(Juliet Capulet)[4]是前工业化时期地中海模式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有些极端;更常见的情况是17岁或18岁的新娘嫁给一个比她大10岁或12岁的男人。
欧洲北部的晚婚年龄和较低的生育率使黑死病对收入的促进作用比欧洲大陆南部持续得更久。毫无疑问,马尔萨斯会很高兴听到他的“预防性抑制”似乎正在发挥作用。
黑死病是推动小分流的第一个冲击。虽然受到同样的瘟疫打击,但由于不同的婚姻模式和农业结构,北海地区的收入得到了长期的提升,并追赶上了地中海地区。第二次冲击发生在瘟疫150年后的15世纪90年代,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推动北海地区的收入远远领先地中海地区。
亚当·斯密[5](将在下一章中占据重要篇幅)写道,“发现美洲和途经好望角至东印度群岛的航道,是人类历史上记载的两件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虽然这种说法有相当程度的夸张,但哥伦布(Columbus)“发现”美洲和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道好望角开辟一条从欧洲直接进入印度洋的新航路,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两次航行——以及麦哲伦(Magellan)在16世纪20年代前后的环球航行——不仅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而且将英国移到了世界的中心。任何在15世纪90年代之前绘制的已知世界的半正式地图都会显示英国是位于极西北部的一个岛屿,只比荒凉的格陵兰岛和冰岛更近一点。16世纪后,地图呈现出熟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格局,不列颠群岛处于中心位置。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被称为三角贸易的残酷的大西洋商业诞生了:贸易货物从欧洲被运到非洲换取奴隶,然后这些奴隶再被运到新大陆。三角贸易中的最后一环是那些从新殖民地返回欧洲的船只,上面满载着新大陆的货物。与此同时,在印度洋,配备火药武器的欧洲人强行介入了环绕着东非、印度西部和阿拉伯南部的海岸之间有数百年历史的贸易网中。
这种在非常有利于欧洲人的条件下、以武力和暴力为支撑进行的全球贸易的扩张,其影响与黑死病的影响一样重要。
鉴于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是由葡萄牙王室赞助的,而热那亚人哥伦布的探险是由西班牙人赞助的,人们可能会认为收益是由南欧而非北欧获取的。但是,尽管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引领了这一进程,他们很快就被荷兰人和英国人超越了。
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来看,北海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劳动力市场专家所说的“劳动力供应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工人是否愿意通过减少假期和延长工作时间来应对对其劳动力的更高需求(或者,换句话说,雇主是否有能力强迫工人延长工作时间)。在北海地区,劳动力供应是灵活的,而在地中海周围则不那么灵活。
15世纪或16世纪初,典型的英国工人每年工作160至180天,或不到半年的时间——对现代人来说,这听起来相当令人愉快,直到他意识到这些人是多么贫穷。宗教改革的到来减少了通常作为假期的圣日和其他宗教节日的数量,并在1600年左右将每年工作天数增加到260天左右。随着“圣星期一”(即工人们在周一不来上班,并宣布他们在庆祝圣星期一节)的做法结束,另一波扩张浪潮在18世纪到来了。
这种每年工作天数的增加被称为“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既是后来工业革命的重要前奏,也是持续到19世纪的一个过程。它是由荷兰人和英国人领导的,后来传播到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众所周知,在20世纪初的著作中,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其归功于宗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他认为,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徒(Calvinists),是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驱动力。不过,这一论点当然远未得到普遍认同,例如,加尔文主义在英格兰从未特别强势。一个更常见的现代解释是,全球商业的增长和早期新兴工业的兴起创造了大量新的消费品,而这些消费品以前在欧洲根本不存在,或者完全是普通工人所不能企及的。因为渴望得到茶叶、胡椒、亚麻大衣和瓷盘,工人们准备延长工作时间,以提高他们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当然,虽然劳动力供应的灵活性可以解释1500年至1750年间荷兰和英国收入的部分增长,但它不能解释全球商业如何逐渐由北海国家所主导的整个故事。一个完整的解释需要从“纯经济学”中走出来,并着眼于更大的政治格局。
经济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而许多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政治很重要。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因其在经济史和制度方面的工作而获奖,并为思考国家和政治在经济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的作用提供了最有用的框架。
比较简短的说法是,制度是解释长期增长的一个因素,有时甚至是那个关键因素。不过,当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写到制度时,我们需要搞清楚他们的确切所指。这个意义上的制度不一定就是非专业人士听到这个词时所想到的。一个“机构”不一定是指人们可以敲开其前门的一个实际的组织。相反,它指的是我们可以称为“游戏规则”的东西,一个包含有门可敲的实际机构、法律框架、政府系统,以及同样重要的,制约政治和商业交易的非正式的、往往是不成文的行为准则的更广泛的集合。一个具有良好制度结构的经济体通常被认为是这样的:达成交易的双方可以确信不会突然面临交易被叫停或货物被扣押的情况;银行家在进行贷款时知道贷款有很大可能会被偿还;政府不可能为了偏袒一个利益集团而突然撕毁整个法律框架。这些都不应该被视为“理想的政府应该什么都不做,只需确保产权得到执行,其他方面则以放任自由的方式袖手旁观”的一种论据。
以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时期的西班牙为例,16世纪末是该国的黄金时代。菲利普统治下的西班牙无疑是一个全球大国,至少在表面上是,由于征服了南美洲大部分地区及其银矿而大发横财。然而,菲利普却被称为“来自地狱的借款人”,一个在其统治期间四次拖欠贷款的君主。荷兰在他在位期间反抗了西班牙的统治,它没有西班牙的财富和辉煌,当然也没有一个盛产奴隶和白银的庞大新大陆帝国,但它有强大的商业文化、运作良好的行会和有效的合同法。荷兰的经济体制给了荷兰一个稳定的环境,而西班牙尽管看起来很强大,但它缺乏这种稳定。
与制度框架同样重要的是政府执行框架的能力。国家能力——一个政府确保它所说的应该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的能力——很重要。好意图可能比坏意图要好,但是如果它们仅仅停留在意图的阶段,则几乎毫无用处。
这里有一个权衡:一个国家需要强大到足以执行财产权,但又不能强大到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游戏。
诺斯概述了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以来定居耕作时代的两种国家类型:“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s)和“开放准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
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秩序以及诺斯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整套理论的关键是“经济租金”的概念。没有人真正喜欢支付租金,尤其是经济学家们。但经济学家往往比普通人更广泛地使用这个词。
经济租金不是指为租赁一件物品——无论是一辆汽车、一套公寓还是一台机器——所支付的价格,而是指一些更技术性的东西。它指的是对土地、劳动力或货物的超额支付,超过了所有者实际接受的价格。举一个更接地气的例子:如果一个房东准备以每月500英镑的价格出租一套公寓,而得到的报价是550英镑,那么可以说,他会收到每月550英镑的租金,赚取每月50英镑的经济租金。同样地,如果一个工人很乐意以每小时15英镑的价格从事某项工作,并以每小时18英镑的价格得到了同样的工作,那么可以认为他每小时赚取了3英镑的经济租金。
在理想的和绝对不现实的微观经济学家所谓的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的世界,不存在经济租金一说。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里,有无限多的潜在买家和无限多的潜在卖家,而两者都被假定为具有完美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如果商品和服务的买家和卖家完全了解其他买家和卖家如何给每一种商品或服务估价,那么竞争将迫使价格达到一个没有经济租金的水平。如果租房者知道房东会以每月500英镑的价格成交,那么他们就会按照这个价格去报价。如果雇主知道雇员会接受每小时15英镑,那么他们就不会以18英镑的价格提供工作。
当然,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完美信息或完全竞争的世界里。也未曾有人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市场缺陷的存在——无论是卖家和买家的数量实际上都不是无限的,还是没有人真正拥有完美信息的事实——都意味着经济租金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虽然没有人介意偶尔一两个工人每小时多拿超出他们预期一两英镑的工资,但以比实际价格每月多几百英镑转手公寓的想法往往会引起更多的不满。
所有这些从市场监管者的角度来看可能听起来很有趣,但与诺斯的有限准入秩序和开放准入秩序的发展几乎没有关系。但正是经济租金的存在,支撑着很大一部分的国家发展。经济租金是一种实际上并不生产任何额外物品的致富途径。房东每月获得比他们预期多50英镑的收入,基本上是每年白白获得600英镑。对经济租金的控制和分配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过去一万年左右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经济租金的控制都是通过暴力实现的。
在诺斯的概念框架中,他礼貌地称之为“暴力专家”(不那么礼貌的词是“暴徒”)的人群能够通过承诺保护他人免受暴力专家(比如他们自己)的侵害来组织社会。一旦狩猎采集时代结束,定居耕作时代开始,一些大块头的人类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意识到,从块头没那么大的人管理的田地中获取作物,在某些方面可比自己实际种植小麦要简单、直接得多。诺斯所说的“有限准入秩序”国家就是从这些群体发展出来的。而直到最近,它还是人类组织的主导形式。最终,最成功的“暴力专家”获得了公爵、男爵或国王等头衔。
在这样的国家里,暴力得到控制,秩序和稳定(在大部分时间里)得到实现,因此通过规模经济、更加专业化和更多贸易可以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但是,有限准入秩序的制度设置是偏向精英阶层的——偏向暴力专家和最初暴徒的后代。游戏的规则是被操纵的。
这种秩序的特点在罗马帝国和旧制度法国以及两者之间的大多数定居社会中有迹可循——精英阶层通过暴力控制国家,贸易权利受到限制,并受到一套通常很复杂的规则的制约,精英阶层的财产权往往受到保护,而其他人的财产权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这样的制度使经济得以增长,但也是创造经济租金的理想工具——将某些商品的垄断权授予精英阶层的亲朋好友,几乎可以保证他们获得巨大的财富。有限准入秩序通过控制暴力创造经济租金的夹层,然后在精英阶层之间进行分配。
这听起来可能是对国家的形成历史的一种相当令人沮丧的看法,但总体上与实际情况相符。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曾经只是半开玩笑地指出:“如果说黑社会代表了最顺利的有组织犯罪,那么发动战争和缔造国家就算得上有组织犯罪之典范,是具备合法性优势的典型的黑社会——有资格成为最大的有组织犯罪的案例。”中世纪的君主们,实际上充当着类似于黑帮头目的功能,通过威胁来勒索钱财。
相比之下,诺斯的开放准入社会的特点是较少地创造和控制经济租金,是有更多的竞争——包括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这类国家的特点是:法治适用于精英阶层;外人有进入精英阶层的途径;军队(及其暴力威胁)在政治上受更正式的框架控制,而非统治者的一时兴起。在诺斯的模式中,从有限准入秩序到开放准入秩序的过渡是充满困难和挑战的。没有多少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但对诺斯来说,它是成功经济根本的驱动力。注重真正的竞争,而不是分割租金流,推动着企业和企业家走向创新和完善。
没有人会严肃地声称,17—18世纪的荷兰共和国或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法案》(Act of Union)之后的新生大不列颠王国就是诺斯所说的“开放准入秩序”。但许多人都会认同,荷兰共和国和18世纪的大不列颠王国肯定比法国或西班牙等国更接近这样一种秩序。在这两个国家中,强大的立法机构都得到了发展,精英阶层的圈子得以扩大(固然,只是从“极少数”到“少数”而已),行政权力得以被施加了一些限制。在这两个国家中,商人利益集团都有能力针对更广泛的政策问题行使一些发言权。当然,英国国王从未拥有过完全的权力——他们总是不得不让主要的贵族们参与进来,到了近代早期,这个圈子已经扩大到包括主要城市,特别是伦敦最富有的公民,以及农村的大人物。
在工业革命的前夕,英国正逐步从有限准入秩序过渡到开放准入秩序。
有悖常理的是,与法国相比,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后更加“自由”(尽管当时这个词还没有这个含义)的英国政府框架,实际上却使国家更加强大。与海峡对岸的对手法国相比,18世纪初的英国政府凭借其议会制衡机制,在许多精英眼中获得了更广泛的政治认同和更多的合法性。其结果是,“自由主义者”英国能够发展出一个远比“绝对主义者”法国更有效、更强大的国家。到18世纪50年代,英国政府可以收取相当于每人109克白银的税款,而法国和西班牙的税款不到50克。
对政府行动的约束有助于精英们对允许国家机器掌握更多的权力感到更加放心——国家机器被反过来用于对付他们的可能性更小。从17世纪50年代起,英国的“财政革命”(fscal-warfare)得到了发展,由此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得以建立,并通过日益复杂的税收制度和体面的借贷来承担海军的开销。英国对外通过赢得战争和殖民地集中权力,对内通过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在整个不列颠群岛创造了一个单一的大市场。相比之下,18世纪80年代法国或西班牙的商人在将货物运往全国各地时,仍将面临内部关税费用。这种内部关税边界是当地地主的经济租金的极好来源,但很难有利于推动增长或竞争。
荷兰人和英格兰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发展起来的国家能力和制度使他们从1500年开始的世界格局重塑中获得的好处远远超过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而他们也确实获得了好处。从1689年到1815年——所谓的“漫长的18世纪”——英国上升到了世界强国的地位。在这整整126年里,英法之间至少有64年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大多时候,英国是赢家。虽然英国在人口方面与它的对手相比相形见绌,但它在海军事务中保持领先地位的能力加上向大陆盟友支付慷慨的“补贴”的能力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借贷和相对轻松地提高税收的能力比最基本的人力更重要。
18世纪末的英国是相对繁荣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运作良好的农业部门,城市化进程也已经开始,而且最重要的是,尽管它还不是一个工业社会,但肯定已经是一个商业社会。当时货币已被广泛使用,且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即财产私有制和大多数工人出售他们的劳动换取现金的需要,都已经存在。对资本主义诞生时间的追溯依然存在争议,但在向工厂和“血汗小作坊”转移之前,它肯定早就存在了。
看起来马尔萨斯的桎梏已经被甩掉了,或者至少是严重松动了,在劳动力愿意比以前工作更多天数和时长的背景下,许多工业革命后的关键时代特征已经开始确立。16世纪以后,劳动力供应的灵活性,以及至关重要的,更高效的政府,使得荷兰和英国——特别是英国——能够从新贸易中获益。
然而,这三百多年的历程只是一个开始。工业革命给已经存在的趋势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使人均收入真正腾飞,英国的实力在未来几十年内呈几何级数增长。在19世纪中期的一个短暂时期,英国可以说是唯一的全球大国,而这种实力是建立在其工业经济的基础上的。
是什么引起了英国“起飞”和向现代增长的过渡,即“发明之发明”,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对英国从18世纪80年代的商业经济过渡到19世纪30年代的工业经济的各种解释,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两者都试图解释,为什么在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有限的生产率增长和相当停滞的生产方式之后,这一切在这些关键年份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创新突然成为常态?
对一些人来说,关键的驱动力是文化和思想。从16世纪和17世纪开始在整个欧洲发展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和随后的“文人共和国”[6]为现代经济增长拉开了关键序幕。在印刷术和分裂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相比)的帮助下,反叛者甚至是“异端”的思想家们找到了一个可以继续写作的庇护所,科学和理性得以在欧洲蓬勃发展。
近代早期的欧洲在思想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争夺君主和商人的赞助时创造了一个遍及整个大陆的思想市场,有助于学习、科学和实验文化的扎根。也许有一万名欧洲知识分子属于这个跨国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成就和成功是以原创性和通过实际实验支持理论主张的能力来衡量的。围绕伊拉斯谟(Erasmus)、弗朗西斯·培根和艾萨克·牛顿的思想而发展起来的机构见证了现代大学的建立和学术界的标准程序,如对证据发展的诉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1500年明显落后于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的欧洲科学,到1800年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再加上荷兰或英格兰的商业文化创造了一种氛围,在那里,赚钱不再被视为令人厌恶的事情,实际上反而是值得欣然接受的事情,有时甚至是美德,在这种氛围中,创新的腾飞只是时间问题。重视学习和独创性的文化,加上通过它而获得收入的潜力,可能是创造性突然增加的必要因素。
一个更加唯物主义的学派更强调从传统经济角度而不是文化的发展来看待激励措施和成本结构。18世纪80年代的英国具有历史上不寻常的综合特征:与邻国相比,相对较高的工资;易于获得的廉价能源(包括煤田和水力),低廉的借贷和资本成本(英国金融制度发展的结果)以及一个没有内部壁垒的大市场。
17世纪末的早期突破很难说是“科学”,它们是有待解决的更直接的工程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先进的知识,而是需要时间和资金。
唯物主义者认为,工业革命早期的许多关键发明都偏向于用资本(机器)代替劳动来生产商品。对于那些面临高额工资账单但资金成本低廉(和能源成本低廉)情况的企业家来说,任何使用更多资本和更多能源,同时减少劳动力成本的方法都是有意义的。这种成本组合仅存在于英国。这是一种“诱导创新”[7]的理论,认为工业革命的发生仅仅是因为有适当的激励机制。无论是珍妮纺纱机还是水力纺纱机——棉花生产的关键突破之所以出现,并非因为一些可以追溯到伊拉斯谟的深刻科学思想,而只是因为棉花制造商希望有一种方法可以更廉价地制造棉花,并且他们有钱为实验提供资金。
人们可以认为文化和思想推动了新发明的供应来调和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思维方式,但正是英国的物质条件和激励措施推动了对这些发明的需求。真正毋庸置疑的是,过往的情况很重要:黑死病后人均收入的增加、婚姻和生育模式、英国政府的实力及其在17世纪和18世纪全球商业中的作用。
历史学家们还将在未来几个世纪里继续争论是什么导致了工业革命,但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一个唯一的答案。不过,归根结底,真正重要的是,革命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它所发生的地方。英国首先改变了,然后世界改变了。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
注释
[1]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1916—2003)以工业革命为背景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论”。在该理论中,核心阶段被比喻成“起飞”阶段,这个阶段大概会持续10~20年:在此期间,国民收入增长率将出现急速的飞跃和质变;同时,国民储蓄率会增加将近1倍,“主导部门”的出现为经济体中其他部门的发展设定基调。“起飞”阶段的绝佳范例即为英国的工业革命。——译者注。
[2]原始全球化(Proto-globalisation)或早期现代全球化是继古代全球化之后的大致跨越1600年至1800年的全球化历史的一个时期。该词最初由历史学家A.G.霍普金斯(A.G.Hopkins)和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提出,描述了贸易联系和文化交流日益增长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在19世纪所谓的“现代全球化”出现之前的那个时期。——译者注。
[3]指《强权与富足》(Power and plenty:trade,war,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译者注。
[4]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女主人公,住在意大利维罗纳。——编者注。
[5]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所著的《国富论》是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这本书发展出了现代的经济学学科,也提供了现代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译者注。
[6]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是欧洲和美洲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后期的一个以通信方式组成的学者和文学界人士社区,促进了启蒙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或法国所谓的思想家之间的交流。——译者注。
[7]诱导创新(Induced innovation)是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于1932年在其著作《工资理论》(The Theory of Wages)中首次提出的微观经济学假说。他提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本身就是发明的动力,也是特定种类发明的动力,旨在节省使用相对昂贵的生产要素的成本。”——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