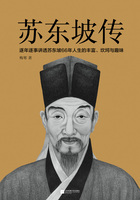
第4章 气盛才子,冷面上司
嘉祐八年(1063)三月,于大宋王朝来说是一个愁云惨淡的月份——仁宗在这月崩于福宁殿。
四月一日,皇太子赵曙即位,即后来的英宗。
英宗自少体弱多病,当时正患疾在床,只是徒担着皇帝的虚名而已,朝中政事基本由他的母亲光献太后处理。
此时的苏轼远在凤翔,朝局的变动对他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凤翔的人事调整让他接下来的日子颇不好过。这年,宋选罢任,原为京东转运使的陈希亮代之。
陈希亮,字公弼,“天资刚正”是他最醒目的标签,苏轼才与他交锋,便深有感触。
这位来自四川眉州青神县的上司,不仅是苏轼的同乡,论起辈分,还是他爷爷辈的人。老乡加长辈,按照人之常情,陈希亮应该比他人更加照顾苏轼才是。
事实却完全相反。在苏轼的眼里,陈希亮就是一个铁面无私,甚至刚愎自用的可恶老头。这个身材矮小、面目清瘦的上司,整日绷着一张冷脸,眼睛在堂上扫来扫去,扫到的总是下属与同僚的缺点与短处。作为他的助手,苏轼更是在被挑剔之列。
苏轼曾自述来凤翔的任务,其中一项便是“兼掌五曹文书”。这对参加过制策考试的苏轼来说,自是不费功夫。陈希亮却不这么看,面对苏轼递上来的文书,他那双严目恨不得每个字都不放过。结果,那些苏轼自以为得意的文书,总是被陈希亮涂改得面目全非,改过再扔给苏轼重写。
如此三番五次,弄得苏轼心中很是窝火,但上司的话就是命令,还是要按照要求去改。
其实,在凤翔,陈希亮不仅不受苏轼待见,他的下属、同僚,也多不喜欢他。士大夫们应酬宴游,席间莺歌燕舞,欢声笑语一片,但只要陈希亮出现,满座便鸦雀无声,即便还有人说两句,也不过是无味的应酬之语。
因此,那些有陈希亮在场的应酬,苏轼便不喜欢参加。
对于苏轼的想法,陈希亮心知肚明,但他丝毫没有打算收敛,反倒有变本加厉之势。
苏轼当初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中制策三等,又加上他为人豁达随和,在凤翔,除了陈希亮,上上下下都颇喜欢他。有一个当差的小吏,每次见了苏轼都直呼他“苏贤良”。
陈希亮听到后,极不高兴——不过一个小小的判官,什么贤良不贤良?他将那个小吏狠狠地训了一顿还不够,又赏了他一顿板子。
那板子落在小吏的身上,更落在苏轼的脸上。自此,他更是将陈希亮恨在心里。天生一副硬骨头的苏轼,绝不肯向这位上司低头。后来,苏轼送了陈希亮一首极具讽刺之意的诗,陈希亮看后不过一笑置之。
依照惯例,中元节时长官要在官府中摆宴,大小官员都得参加,这是工作宴,也是政治宴。
嘉祐八年(1063)中元节,月朗风清,苏轼在家里置酒,请了三五好友,喝得不亦乐乎。
在那三五好友中,有那个呼他为“苏贤良”的小吏,还有陈希亮的小儿子陈慥。他不但没去参加陈希亮摆的官宴,还明摆着与陈希亮唱起对台戏。这赤裸裸的反抗带来的后果是,苏轼被罚铜八斤。
当时,罚铜是对官员获罪的一种处罚。
宋朝时,每一千文铜钱的标准重量通常是五斤,八斤铜等于一千六百文。对于一个靠官薪吃饭的小官来说,这惩罚实在是有些重了。
苏轼不是记仇的人,但他心里还是郁闷至极。陈希亮则像无事人一样,罚过了似乎也就解气了,依旧如往常一样对苏轼支来使去。
陈希亮居住的太守府紧邻终南山。终南山之高,终南山之秀,曾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竞折腰。陈希亮有近水楼台之便,却在到任好久之后才发现此处原是风景胜地。拄杖漫步于其下,露出在林木上面的山峰一座接一座,就像有人在山外行走,只见发髻一般。陈希亮的好奇之心与闲情逸致被彻底唤醒了,他决定在那个最佳的位置建一座高台以观山景。
就这样,没过多久,凌虚台便耸立在了太守府的院子里。
亭台建成,自然要写点什么。古往今来的名亭名台记,不外乎对亭台风景之胜或对建台者的功业大加赞颂。陈希亮有无此心不得而知,反正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差事交给了苏轼。
苏轼极少写凌虚台本身,而是大发感慨。归根结底,也就一句话:自古至今,事物的废兴成毁接连不断,沧海桑田,凌虚台最终也逃不过埋没于荒草原野的命运。
新台初建,合府上下喜气洋洋,欲大贺一番,苏轼却打算给陈希亮泼一盆冷水。读过此文的同僚皆替他捏了一把汗——对陈希亮,他顶撞得已经够厉害了。
苏轼谢过同僚的好心提醒,将《凌虚台记》一字未改地递交了上去。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陈希亮竟对那篇铭记大加赞赏,他没有丝毫不快,倒是让人赶紧刻碑,堂堂正正地立在凌虚台上。
陈希亮的反常举动,让苏轼颇为意外,尤其是陈希亮讲的那番话,更让苏轼感动,为自己的狭隘而惭愧。
陈希亮说:“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指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
可以说,陈希亮对苏轼的把脉是准的,才高者往往气盛,苏轼的仕途一波三折,谁说不与他的这种个性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