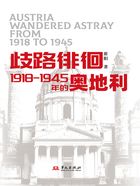
三、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折冲
1919年1月18日,旨在安排战后国际秩序的和平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围绕着怎样惩处战败的德国这一重大议题,实际主导会议的英、法、美三国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对德奥合并的看法,三国也大相径庭。

油画《巴黎和会》(威廉·奥尔本绘)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英国就已倾向于拆解奥匈帝国。到1918年下半年,英国看出奥匈帝国在战败和“民族自决”思潮的双重冲击下已是穷途末路。但直至巴黎和会召开前,英国仍然没能就新独立的奥地利制定出一个相对成熟的政策。英国外交界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主张尊重奥地利加入德国的意愿,让德奥两国自由合并;另一种是建议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从奥匈帝国分裂出来的国家组成一个“多瑙河邦联”。支持德奥合并的人士提出的理由是:天主教的奥地利并入新教的德国能够冲淡后者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氛围,况且目前看不出德奥合并对英国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危险”;剥夺奥地利行使“民族自决”的权利将滋生新的民族问题,还会把奥地利推向德国,成为下一次大战时德国的忠实盟友。赞同“多瑙河邦联”观点的人士则认为奥匈帝国消失以后,德国必然会向巴尔干地区渗透势力。为了维持中欧的稳定,一个类似于旧奥匈帝国的邦联制国家还是有必要存在的。
1918年11月9日,英国一家名为《新政治家》的刊物登出文章,称奥匈帝国的崩溃使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与德国重新建立了联系,他们想要“回家”与德国同胞生活在一起,这是“一种我们应该尊敬和理解的愿望”。由于《新政治家》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政治倾向很接近,所以外界猜测它实际反映了劳合-乔治和英国政府对德奥合并的看法。不过,“一战”才刚结束,英国民众对不久前还在战场上厮杀的敌人德国普遍感到厌恶和怀疑,坚持必须要让德国在领土上付出代价,德奥合并也被视为对英国安全的潜在威胁。11月5日《泰晤士报》称,有大量证据表明德国正在试图“用谈判获得那些凭武力得不到的东西”。有鉴于此,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上比较谨慎。他想劝阻德奥两国先不要急于求成,奥地利应暂时保持独立,将来再视形势的发展做决定。
法国的态度比英国明确得多。“一战”末期,法国国内也有过支持德奥合并的观点,但没多久就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从政府到民间的一致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胜令法国民众心有余悸,对能否再次打败德国缺乏信心,全社会上下都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这个宿敌。历史学家、记者雅克·班维尔撰文警告说,魏玛共和国与德意志帝国没什么区别,德国的势力迟早还会越过莱茵河。法国在中欧有着广泛的利益需要保护,革命后的俄国又已指望不上,如果德奥合并就意味着将来4000万法国人要单独对抗8000万德国人。他力主保留奥匈帝国的框架,组建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邦联制国家。
1918年10月16日,一向被看作是法国外交部喉舌的《时报》发表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称“不管何种代价或条件,我国都不能允许奥地利并入霍亨索伦帝国……无论德国政府首脑是鲁登道夫还是谢德曼,也无论德国奉行俾斯麦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德奥合并都不属于民族统一的范畴,而是普鲁士国家想迫使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德意志族群屈服于它。”基于这种心理,法国虽然与奥匈帝国是交战国,却并不想看到后者解体。11月初,法国根据一些情报研判德国有向奥地利进军的迹象,曾一度想在德国之前直接出兵抢占奥地利。12月29日,法国外交部长斯特非·毕盛在一次议会辩论中清楚地表达了对德奥合并的警惕。他说,德国利用德奥合并不仅可以在领土问题上“堤内损失堤外补”,而且还能顺势控制东南欧地区。法国作为战胜国,决不能眼看着位于中欧核心地带的奥地利被德国吞并。
1919年2月,随着奥地利议会选举结果揭晓和德奥秘密谈判一事逐渐浮出水面,法国的态度愈加强硬。法国舆论分析,德奥合并不是出自奥地利的本意,而是受到了德国怂恿,法国必须坚决反对这种“纯粹人为的煽动”。3月,《时报》接连多期不厌其烦地提及奥地利和莱茵兰一样是“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安全保障”。《时报》还忧心忡忡地再次论证了班维尔的观点:法国人口增长缓慢,而德国是一个拥有6600万人口的大国,以后还有可能加上700万奥地利德意志人和200万波希米亚德意志人,法国正在慢慢地输掉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巴黎和会的主角之一、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扬言,他无意为法国的敌人增加领土和人口,必须确保奥地利的永久独立。
英法在德奥合并问题上的迥异立场,反映了战后两国欧洲政策的差别。英国从传统的维持欧洲均势的角度出发,不愿法国一家独大,反对过分宰割德国。而且英国认为,公然违反“民族自决”原则会使协约国在道义上居于劣势。法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屡遭德国祸害,它把德国战败看成重夺欧洲霸权的绝佳机会,必欲最大程度削弱德国。对于奥地利,英法两国本没有什么成见,也深知它的糟糕处境,但如果让奥地利与德国搅和在一起,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英法都无意让德奥合并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拖延巴黎和会的进程,于是想借重一下美国的意见。
美国一向在欧洲事务上持比较超然的姿态。威尔逊总统是一位充满自信的理想主义者,很难说他的“十四点计划”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曾为威尔逊撰写《当前形势:战争目的与和平条款》备忘录 的著名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和《纽约世界报》编辑弗兰克·科布认为:奥地利人有权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过别指望有人会帮他们抵挡来自法国的阻力。虽然奥地利各界对威尔逊寄予厚望,一些奥地利人还在1918年11月16日向威尔逊发起请愿:“总统先生既然已将民族自决权交给了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让他们在奥地利周边建立了民族国家,我们相信你也一定会把同样的权利赋予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民。”但按威尔逊的本意,“民族自决”只是用来解放那些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的,至于它是否适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德意志族,连威尔逊本人也没想清楚。在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前,威尔逊不太了解德奥合并的深层原因,以为这只是一个由奥地利经济困难而引起的突发事件。随着欧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奥地利要求与德国合并的呼声就会自然消失。后来一些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学者考证说,威尔逊到巴黎后受了法国的欺骗,才放弃了对德奥合并的支持,这是缺乏根据的。其实,威尔逊的奥地利政策一直很模糊,他也并不真正关心奥地利的前途。
的著名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和《纽约世界报》编辑弗兰克·科布认为:奥地利人有权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过别指望有人会帮他们抵挡来自法国的阻力。虽然奥地利各界对威尔逊寄予厚望,一些奥地利人还在1918年11月16日向威尔逊发起请愿:“总统先生既然已将民族自决权交给了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让他们在奥地利周边建立了民族国家,我们相信你也一定会把同样的权利赋予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民。”但按威尔逊的本意,“民族自决”只是用来解放那些受压迫的弱小民族的,至于它是否适用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德意志族,连威尔逊本人也没想清楚。在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前,威尔逊不太了解德奥合并的深层原因,以为这只是一个由奥地利经济困难而引起的突发事件。随着欧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奥地利要求与德国合并的呼声就会自然消失。后来一些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学者考证说,威尔逊到巴黎后受了法国的欺骗,才放弃了对德奥合并的支持,这是缺乏根据的。其实,威尔逊的奥地利政策一直很模糊,他也并不真正关心奥地利的前途。
1919年3月1日,在巴黎和会的一次全权代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兰辛表示,目前他尚不了解美国政府对德奥合并持何种立场,但他个人相信,任何想阻止德意志民族最终统一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两天后,兰辛又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如果反对德奥合并的建议是由某个大国提出的,那其他国家都应认真对待,不过这不代表美国一定要在关乎欧洲领土变动的重大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兰辛模棱两可的说法表明美国既要避免违反“民族自决”原则,又不至于因为同英国站在一边而与法国伤了和气。所以美国始终不肯出头,而是暗中居间协调,力求促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3月15日,法国和美国一起在巴黎和会的领土问题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德国必须承认奥地利的独立地位,但“四大国”中的另外两国——英国和意大利对此很不满意。英国仍然反对过早决定奥地利的未来。意大利是四大国中最弱的一个,对法国和德国都十分忌惮,不愿让其中任何一国主宰中欧事务。奥匈帝国解体后,意大利少了一个劲敌,让中欧保持碎片化对它来说是最为有利的。根据1915年4月意大利与协约国缔结的《伦敦密约》,原属同盟国阵营的意大利加入了协约国一边作战。作为对意大利临阵倒戈的奖赏,战后协约国默许它占领了原属奥匈帝国的南蒂罗尔和的里雅斯特等地。意大利深知这几块领土来路不正,害怕德奥一旦合并,德国就会向它讨要居住着大量德意志族的南蒂罗尔。然而,意大利更不想看到北方再出现一个强大的、以奥地利为核心的“多瑙河邦联”。所以意大利摇摆不定,既想留下一个独立的奥地利作为缓冲地带,又担心孱弱的奥地利会被德国合并或受法国控制。英法等国虽然瞧不起有过反水行径的意大利,但由于意大利是奥地利的重要邻国,对它的态度也不能不予以一定重视。因此,四大国在德奥合并问题上的意见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为消除大国间的分歧,避免拖延和平协议的签署,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磋商,四大国会议还是在4月22日采纳了法美两国的提议。5月2日,法国在四大国会议上再次提出应让奥地利永久独立。威尔逊首先肯定了法国的意见,之后又说任何民族都不会被永远禁止行使民族自决权,等于又间接地支持了英国。5月6日,协约国正式宣布德奥两国3月2日签订的合并协定无效。
协约国的禁令顿时在德国和奥地利掀起了轩然大波。驻柏林的哈特曼主张德国政府尽快发表声明抗议这项禁令。5月9日,外交部长布罗肯多夫-朗曹气愤地宣布德国将继续履行3月2日的合并协定。他驳斥德国要拿奥地利与协约国做交易的传闻是“一派胡言”。布罗肯多夫-朗曹还起草了一份提交协约国的文件,重申德国仍将推动德奥合并。5月29日,德国以强硬的措辞称“民族自决权不能普遍适用,严重损害了德国的利益”,并坚持在《魏玛宪法》中保留有关德奥合并的条款。奥地利方面,5月11日和12日伦纳接连在维也纳的民众集会上讲话,保证奥地利政府决不放弃德奥合并。鲍威尔则坚信,奥地利还远没到缴械投降的地步。
5月26日,鲍威尔给率领奥地利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的伦纳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讨论了协约国内部和中欧局势变化可能给德奥合并带来的转机。鲍威尔推测,协约国一定会意识到允许德奥合并的代价要比维持奥地利独立低得多。但是,奥地利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处处碰壁。代表团曾向协约国辩解说,奥地利也是一个新生国家,不应为奥匈帝国的战败负责,但协约国根本不听这套说辞,仍将奥地利和匈牙利一起作为奥匈帝国的继承国对待。伦纳等人也没有获得与协约国代表当面谈判的资格,只能以书面形式递交意见,至于能不能被采纳就听天由命了。情绪越来越悲观的伦纳觉得奥地利代表团待在巴黎已无事可做,只剩下等待审判结果了。
尽管德奥两国直到7月底仍在拼命研究德奥合并的各种替代方案,尽一切努力延续越来越渺茫的合并希望,但进入8月,奥地利恶化的经济成了压垮德奥合并的最后一根稻草。1919年上半年以来,奥地利政府支出超过收入的200%,法定货币克朗大幅度贬值,私人企业成批倒闭,失业人数高达18.6万人。对一个人口不到700万的国家而言,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奥地利本以为德国会慷慨解囊,不料德国方面却说,它的经济状况同样十分困难,自顾尚且不暇,更别提帮扶奥地利了。鲍威尔强调奥地利不是一般的外国,而是即将成为一家人的“德意志兄弟”,但德国仍然表示爱莫能助。失望之极的鲍威尔沮丧地说,看来两国之间还没有就合并达成“绝对的共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协约国从1918年12月至1919年8月向奥地利输送了价值1亿美元的50多万吨各类物资,协助奥地利度过了战后最艰难的时期。

奥地利货币克朗,正中央印有“DEUTSCH ETERREICH(德意志奥地利)”的字样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伦纳等人的头脑逐渐冷静了下来。既然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奥地利还要依靠协约国维持生存,再一意孤行无疑就是不明智的了。加上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还占着不少奥地利领土,福拉尔贝格、蒂罗尔、萨尔茨堡等地区一直有强烈的分离倾向,奥地利想要保持国家完整也有赖于协约国出面,看样子是该和德奥合并说再见了。主意已定的伦纳坚决拒绝了鲍威尔公开3月2日德奥合并协定的建议,也停止了继续争取协约国允许德奥合并的活动。
1919年9月10日,奥地利代表团与协约国签署《圣日耳曼条约》。该条约第八十八条规定:“奥地利之独立如非经国联行政院之许可不得变更。”此前的6月28日,德国也接受了《凡尔赛和约》,其中第八十条亦规定:“德国应照将来奥国与协约国及参战各国所订之条约中规定之疆界,承认并确切尊重奥国之独立;复承认奥国之独立如非经国际联盟行政院之许可,不得变易。”至此,奥地利的独立地位以国际法形式确定了下来。
平心而论,如果拿《圣日耳曼条约》与《凡尔赛和约》《特里亚农条约》相比较,就会发现协约国对奥地利并不算特别苛刻。如《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必须支付巨额战争赔款,《特里亚农条约》使匈牙利丧失了72%的领土和2/3的人口。而《圣日耳曼条约》并未明确奥地利的赔款金额,只是含糊地将该问题推迟到1922年再做决定,后来实际上不了了之。《圣日耳曼条约》规定奥地利军队不得超过3万人,看起来似乎对奥地利重整军备做了严格限制,但按照《凡尔赛和约》,即使是德国也只能保有一支10万人的陆军和少量海军,并且不许拥有空军。对于面积狭小、没有领海、人口数量仅为德国零头的奥地利来说,能有如此规模的军队已属不易。更何况战后的奥地利既无意愿、也无财力供养一支大型的常备军。直到1936年,奥军总兵力(绝大部分为陆军)才2.2万人而已。
在领土方面,《圣日耳曼条约》也给予了奥地利一定的补偿。虽然南蒂罗尔和苏台德这两个德意志族聚居的地区最终还是被分别划给了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致使原奥匈帝国的1050万德意志族中有将近400万散落在了奥地利境外,但邻国向奥地利提出的其他一些更具挑衅性的领土要求均被协约国拒绝,奥地利在与南斯拉夫划界时没有吃太多亏,还得到了原属匈牙利的布尔根兰,几个原打算从奥地利分离出去的州也留在了奥地利版图内,可谓得失相当。
不过,《圣日耳曼条约》毕竟是英法等国基于自身利益而制定的,从奥地利的角度看,其中充斥着太多不合理的地方。最主要的就是,它既要求奥地利承认是奥匈帝国的继承国,却又逼迫奥地利否定自己的德意志属性;它一手促成了奥地利的独立,却又因为与“民族自决”原则不相符,反而更加削弱了奥地利民众对新祖国的认同感。茨威格说:“因为协约国不愿看到战败的德国因此而变得强大,所以协约国明文规定:这个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必须继续存在。对一个自己不愿意存在的国家竟下达这样的命令:‘你必须存在!’——这是历史上的咄咄怪事。”果然,当奥地利代表团在《圣日耳曼条约》上签字的消息刚传回奥地利,群情激愤的维也纳市民就包围并纵火焚烧了法国驻奥地利使馆。
遵照协约国的指示,奥地利的国名也做了更改,使用了10个月的“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被“奥地利共和国”所取代。协约国竭力避免重新勾起奥地利对德奥合并的幻想,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周边邻国则不想让奥地利再做恢复奥匈帝国的美梦,但将这些愿望都寄托在区区一个国名的变动上是不现实的。只要德奥合并的根源还存在,它就迟早还会有死灰复燃的一天。需要注意的是,《圣日耳曼条约》也好,《凡尔赛和约》也好,都没有明文绝对禁止德奥合并,只是给它加上了“未经国联许可不得为之”的限制。据说,这种留有余地的表述是经劳合-乔治、克里孟梭和威尔逊三人反复斟酌之后才敲定的,是英法美三国相互妥协的产物。
《圣日耳曼条约》签署后,伦纳向英美两国致以了诚挚敬意,感谢巴黎和会期间它们在德奥合并问题上对奥地利的尊重。同时伦纳也隐晦地批评了法国和意大利,他说,新生的奥地利现在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友谊和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