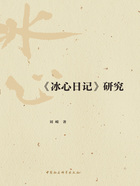
序言
李玲
冰心(1900—1999)是五四时期登上文坛、终身笔耕不辍的文学大家。青年冰心以“爱的哲学”和“冰心体”的文体风格闻名于世。[1]她早年的小说《两个家庭》《超人》、散文《笑》《寄小读者》《往事》、诗歌《繁星》《春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郁达夫1936年引用雪莱吟咏云雀的诗句:“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认为这“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三四十年代,冰心小说《相片》《我们太太的客厅》以及以“男士”为笔名创作的系列小说“关于女人”,六十年代,冰心的散文《樱花赞》《一只木屐》等,皆真挚优美典雅,是那个年代的空谷幽兰。晚年冰心又以“童年杂忆”“关于男人”等系列回忆性散文和《我请求》《无士则如何》等杂感,完成了一次风格上的转型。
冰心一生70多年的文学创作,有两个方面是不变的,一个是主题以爱为中心,另一个是字里行间总表现着作者人格的高洁无染。也有两个方面是变化的,一个是文体方面,早期和中期多为抒情散文,晚年则以杂感和回忆录为主;另一个是语言风格,早期和中期散文偏于清丽典雅,有着“鸭梨儿”的“清脆”,[2]晚年则洗练通脱,时有锋芒显露。冰心创作中这些变与不变的因素,也交织映现在她那些作为私人写作的当代日记中。
冰心经典作品的研究,历经百年,已经比较充分;而关于冰心日记、书信的整理和研究,则还处在初始阶段。刘嵘博士继冰心文学馆原馆长王炳根先生之后对冰心日记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这本《〈冰心日记〉研究》专著,和王炳根论文及其长篇传记《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的相关章节,共同填补了冰心日记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打开了冰心生平研究、冰心私人言说与公开作品互证研究的广阔空间,同时还从一个角度丰富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研究。
关于冰心日记,还请读者看本书的详细阐释,我则简要概述一下我所理解的冰心文学创作特色,为本书的阅读提供一个铺垫,也以此向从事冰心日记研究的青年才俊致敬。
一 万全之爱与乐夫天命
冰心的“爱的哲学”有形而上思考与现实人生关怀两个层面。
时光永恒、人生有限,人常常难免为生命的短暂感到无奈和惶恐。在对生命作形而上思考的时候,青年冰心以“万全之爱”来抵御终极的虚无。在散文《“无限之生”的界线》中,冰心借人物之口表明死亡不过是生命“越过了‘无限之生的界线’”罢了。想象中,死去的宛因[3]对活着的冰心说:“我同你依旧是一样的活着,不过你是在界线的这一边,我是在界线的那一边,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青年冰心在有差别的生命中看到了生死之间、万物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由此超越死亡给生命带来的恐惧,甚至赋予死亡以一层宁静的诗意美,并且在思辨中给孤独的个体生命带来宇宙大家庭的融融暖意。在《往事(一)之二十》中,青年冰心想象中的死亡是“葬在海波深处”,“在神灵上下,鱼龙竞逐,珊瑚玉树交枝回绕的渊底,垂目长眠”,“从此穆然,超然”。在这空灵无迹的浪漫想象中,死亡意境有着生的灵动,却没有尘世的芜杂,从而实现了生命在凡间难以企及的超然、静穆。
晚年冰心,不再构建死是生之延续的浪漫图景,而是坦然接受生命必然会终结的真相,在生死问题上展现出旷达、幽默的智慧。88岁时,冰心在病痛的困扰中,想起老子《道德经》中的句子:“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展示出对躯壳不执念的通脱态度。(《病榻呓语》)她受孔子“骂”原壤“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启发,请人刻了一枚“是为贼”的闲章,嘲弄自己的长寿。(《一颗没人肯刻的图章》)到91岁高龄,她依然既保持着生活的热忱,又了无牵挂地坦然直面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她说:“我自己从来没觉得‘老’,一天又一天忙忙碌碌地过去,但我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忽然死去。至圣先师孔子说过:‘自古皆有死’,我现在是毫无牵挂地学陶渊明那样‘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我从来没觉得老》)
二 母爱、儿童之爱和自然之爱
在现实关怀层面上,冰心终身都是母爱、儿童之爱和自然之爱的歌者,尽管它们的内涵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
歌唱母爱,青年冰心首先是从女儿的角度、以感恩的心情,把母爱理解为遮挡人生风雨的精神庇护所。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三》中,她说“写到‘母亲’两个字在纸上时,我无主的心,已有了着落。”从个人所感受的母爱温暖出发,冰心又将母爱演绎出为整个世界的精神动力。她说:“‘母亲的爱’打千百转身,在世上幻出人和人,人和万物种种一切的互助和同情。这如火如荼的爱力,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的移向光明!”(《寄小读者·通讯十二》)。正是循着这个母爱济世的思路,中年冰心赋予了母爱以承担维持人类正义、反对侵略战争的历史使命,1946年她在《给日本的女性》的散文中说:“全人类的母亲,全世界的女性,应当起来了!我们不能推诿我们的过失,不能逃避我们的责任,在信仰我们的儿女,抬头请示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以大无畏的精神,凛然告诉他们说,战争是不道德的,仇恨是无终止的,暴力和侵略,终久是失败的?”
写作《寄小读者》时期,冰心不过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子,自己还无限留恋真率无伪的童年时代,也希望小朋友们能顺利走过成长时期。她把自己感受到美好事物叙说出来与小朋友共享。她对小读者说:“我是你们天真队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自傲的:就是我此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为止,我恳切的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最热情最忠实的朋友!”早年冰心不是站在一个优于儿童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地以师长面目去教训儿童,而是以平等的态度、用自己热情诚恳的心去与儿童交朋友。晚年冰心则以慈爱的母性心怀把闹嚷嚷的孩子们看作“关不住的小天使”,建议人们春游的时候“只拣儿童多处行”(《只拣儿童多处行》)。
自然事物在冰心的眼中,总显得格外清新优美。碎雪、微雨、明月、星辰,都是冰心所爱,但最打动她心怀的,则是自幼看惯了的山东芝罘岛边的大海。《山中杂记·(七)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中,她列举了海比山强的种种理由之后,甚至极端地宣布:“假如我犯了天条,赐我自杀,我也愿投海,不愿坠崖!”从海中,她看到的是“海阔天空”的境界,是“庄严淡远”的意味,以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妩媚,遥远,璀璨”。海对冰心而言,不仅是富有美感的客观景物,而且能够滋养性情、启迪人生。在《往事·十四》中,她对弟弟们说,“我希望我们都作个‘海化’的青年”,因为“海是温柔而沉静”,“海是超绝而威严”,“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美国波士顿郊外雪中的沙穰青山,在冰心的感受中,“只能说是似娟娟的静女,虽是照人的明艳,却也不飞扬妖冶;是低眉垂袖,缨络矜严”。(《往事(二)之三》)晚年,玫瑰的浓香、桂花的幽香、君子兰的静雅气质仍然滋润着冰心的心田,(《话说君子兰》)而梦中那“清脆吟唱着极其动听的调子”的小翠鸟,更是90岁冰心美丽心灵的外化。(《我梦中的小翠鸟》)
三 针砭现实与怀人忆旧
冰心并非是一个没有锋芒的人。1923年在东京的游就馆中看到中日战胜纪念品和战争图画,她说:“我心中军人之血,如泉怒沸。”她进而阐释自己的愤怒是基于对正义的维护,而不是出于弱者的怨恨。她说:“我心中虽丰富的带着军人之血,而我常是喜爱日本人,我从来不存有什么屈辱与仇视。只是为着‘正义’,我对于以人类欺压人类的事,我似乎不能忍受!”(《寄小读者·通讯十八》)冰心既有强烈的正义感、浓厚的家国情怀,又有超越种族、阶层、性别的人类爱精神。战后在日本,她更是把对日本人民的同情、热爱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否定融为一体两面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她盼望中国社会能健康发展,尤为关注教育问题,写了《我请求》《我感谢》《无士则如何》等杂感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教师群体待遇低的问题大声疾呼。她说:“我只希望领导者和领导部门谛听一下普通群众、普通知识分子的心声,更要重视‘无士’的严重而深远的后果。” (《无士则如何》)
冰心早年虽也有一些怀人忆旧的散文,如1936年创作的《记萨镇冰先生》就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清简自律、体恤下属而又文雅倜傥的海军将领形象,但是冰心大量的自传和怀人散文则写于1978年以后。晚年冰心,“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她在自传中记述了福州谢家祖父宽厚有威、兄弟姐妹和谐有趣的大家庭生活场景,也描绘了童年在烟台海边做父亲的野孩子的性别越界经历,还回忆了初入贝满女子中学、再进协和女子大学、而后又合校到燕京大学、毕业后再到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研究生的求学经历,梳理了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成长历程。她认为:“我比较是没有受过感情上摧残的人,我就能够经受身外的一切。”(《童年杂忆》)怀念故交知己,冰心总是从品格和性情两方面切入,既概述人物的总体特点,也记叙某些有趣的生活细节。她既怀想自己的祖父、父母、舅舅、兄弟,也纪念吴雷川、司徒雷登、吴贻芳、老舍、孙立人、林巧稚、梁实秋这些文化人的嘉言懿行,还记取富奶奶等平凡人的高尚品质。《老舍与孩子们》中,第一次见面,“一转身看见老舍已经和我的三岁的儿子,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狗熊呢”。《记富奶奶——一个高尚的人》中,她深情记述了抗战贫病交加的艰难岁月中,富奶奶与她一家相濡以沫的动人故事。
结语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迷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掉,也不是悲凉。”(《寄小读者·通讯十九》)冰心在散文中展示出的圣洁的济世爱心,曾经温暖了无数在人生跋涉中感到孤寂的男女,引导人性往善良友爱的方向发展。1931年沈从文曾说:“冰心女士的作品,以一种奇迹的模样出现,生着翅膀,飞到青年男女的心上去,成为无数欢乐的恩物。”[4]冰心的爱的文学,仍然是21世纪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冰心文学创作的经典性,奠定了冰心日记研究的意义前提。冰心日记,又自有深化冰心文学研究的价值。刘嵘的冰心日记研究有如下四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第一手资料严谨真实。刘嵘在王炳根先生的带领下一起录入、注释冰心日记。他们遵循“整理时只做标点、断句、分段,文字一律保持原貌”[5]的原则,这最大限度保证了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展示了整理者尊重历史原貌的科学态度。
第二,日记研究扎实深入。本书上编,刘嵘从国际交流状况、国内经济建设、国内文化建设、冰心个人生活四个方面多层次地归纳冰心日记的史料内涵,又将它与冰心创作展开细致的对照研究,从而深入地阐发了冰心日记的价值,深化了冰心史料的研究。
第三,学术视野宽广。本书下编,刘嵘把冰心日记放在当代作家日记比较研究的广阔背景中,从文体风格和日记内容等多方面展开对比阐释,不仅鲜明地揭示出冰心的个性气质和文风特点,也把作为比较对象的茅盾、周作人、叶圣陶等人在日记中所呈现出的个性特点勾勒得十分生动明晰。
第四,语言明白晓畅。这是一本规范的学术专著,却又不晦涩枯燥,语言相当简洁流利。这也展示了刘嵘良好的文风和优秀的汉语写作能力。
总之,这是一本扎实有益的学术著作。它承载了青年才俊刘嵘博士的慧心。
2023年4月3日
北京五道口
[1] 黄英(阿英)1931年在《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版)一书中首次以“爱的哲学”和“冰心体”概括冰心的文学贡献,而后这个说法受到广泛认同。
[2] 周作人:“据我个人的愚见,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清脆,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贡献了。”(《志摩纪念》,《新月》1933年第4卷第1期)
[3] 冰心本名婉莹的谐音。
[4]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文艺月刊》1931年第2卷第4期。
[5] 王炳根:《冰心日记·后记》,载冰心著、王炳根编《冰心日记》,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