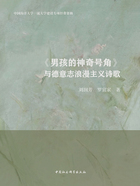
一 历史背景
从历史上看,德意志民族形成较晚,由日耳曼的几个部落融合而成。公元814年法兰克国王卡尔大帝(德语Karl der Große 英语 Charlemagne,约747/748—814)去世,国家一分为三,其中的东法兰克奠定了今天德国的雏形,德语和德语民歌随之逐渐形成。14世纪至16世纪民歌繁荣,有人将民歌的“歌词”用文字记录下来,称之为“歌”(Lied),这就是《号角》最初的底本。以后有诗人效仿,于是“歌”逐渐成为诗的一种形式,所谓“歌体诗”,也被通称为“诗”。随着文学史和民族文学意识的出现,就开始了文学的寻根,有了对民歌的收集、整理、出版,而这些都伴随着德国近代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
德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从15世纪到19世纪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人文主义、巴洛克、启蒙运动、“狂飙突进”、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特点是历时短而进程快。审视这几个思想文化运动,后一个既是对前一个的否定,也是批判性的继承,甚或某种形式的救正。它同时也是从学习外国到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学之林的过程。民歌、民间文学就像一条红线,或隐或显地贯穿其中,而《号角》就是这条红线上的一个“结”,它一头绾住了此前几个世纪的诗歌,另一头又牵出了其后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号角》是德语文学上继往开来的一座里程碑。
简述这段历程要从人文主义说起,它是以意大利为策源地、发生在14至16世纪影响遍及全欧洲的文化运动。它的旗帜是古希腊、罗马,旨在“复兴”以人为本的精神,反对神权,因此也被称为“文艺复兴”。初期它主要从事语言、典籍和编年史的规范、整理工作,以后扩展到哲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德国的人文主义运动始于15世纪,人文主义者们集中在布拉格和维也纳,在整理典籍及与经院哲学的辩论中,写出了一些专门论述语言规律、风格、诗韵、修辞、语法等的专著。这催发了民族情感的觉醒,人们开始注意自己民族的语言、传说、古代的文化,开始了拉丁语和德语的诗歌创作。尽管有人文主义者的艰苦拓荒,但德国的文化较之于英、法、意等国还是大大落后,直到17世纪,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统一的民族语言。由于国家分裂,各地区德语的发音、书写及词义都有不小分歧,同时还混杂着各种外来语。碍于它的俗陋,学者们都使用高雅严密的拉丁语进行著述。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使17世纪的学者们继续人文主义的传统,致力于民族语言的建设。从世纪初开始,“语言学会”在各地相继出现,意在清除外来词、外语语法,确立德语语法、正字法,以建立纯洁规范的民族语言。在自觉建设民族语言的同时,培育本民族的文学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17世纪初的德国文学同样落后,就诗歌而言,还处于自然状态,还没有一定的格律形式。诗歌有两要素,一是语言,二是诗体,于是新一代的诗人就从这两方面入手,开始了他们的筚路蓝缕,而人文主义的教育背景引导他们走上了学习古典之路。他们把古希腊、古罗马的各种诗体以及在意大利、法国盛行的十四行诗引进德国,又像罗马人那样重视修辞学、讲究辞藻,把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的《诗艺》和诗作奉为圭臬,由此形成了德国的巴洛克诗歌。
欧皮茨(Opitz,1597—1639)是这个文学新时代的领军人物,他的《德语诗学》不仅开辟了巴洛克诗歌,而且奠定了德国的民族诗学的基础。他的理论和美学追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歌形式的规范化,二是诗歌语言的纯洁高雅化。有感于法国、英国等借鉴外国形式发展民族文学的经验,特别是受到荷兰的启发,欧皮茨把古希腊和拉丁语的各种诗体系统地引进德国。他认识到语言特点与诗体之间的关系,引进与改造并举,以德语音节的轻重代替拉丁语的长短,把原来的长短交替变成抑扬交替,并让德语诗的词重音落在扬音节上,实现了外来形式的民族化。从此哀歌、十四行诗、亚历山大里亚诗行等外来形式就正式进入了德语诗歌,而德语诗歌也有了自己的堂堂形式,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欧皮茨是理论家,也是一个优秀诗人,他的诗格律严谨,词采华茂,音调流转,代表了巴洛克的典型风格。与欧皮茨同代或稍后的代表性诗人还有格吕皮乌斯(Gryphius,1616—1664),他继续了欧皮茨的传统;霍夫曼瓦尔道(Hoffmannswaldau,1617—1679),他以藻饰著称;卡拉扬(Klaj,1616—1656),华丽之外很有些新气象。其他还有格尔哈特(Gerhardt 1607—1676)、达赫(Dach,1605—1659)、弗莱明(Fleming,1609—1640)等一大批诗人,形成了德语艺术诗歌的第一次繁荣。
历史进入18世纪,这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启蒙时代,启蒙(Aufklärung)的本义是“照亮”,就是要用“科学”“理性”之光驱散中世纪神权统治下思想黑暗,它肯定的是“人”和“人权”,是对人文主义的继承。启蒙运动以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认为一切认识都来自经验,反对基督教神学倡导的盲从,要把人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它的旗帜就是“科学”;而理性主义则从另一个角度冲击宗教的思想禁锢,它提倡唯理是问。“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6]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等从社会、思想、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论述了理性的具体内容,其核心就是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治、思想自由,等等。其实质就是新兴的市民阶级反对封建统治,争取本阶级的权利。启蒙运动最大的政治成果就是法国大革命。
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英、法的影响下展开的,主要表现在思想文化而不是社会政治领域。它接受了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特别是他的学生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的理性主义,认为启蒙的本质在于用理性提升人的道德。因此启蒙作家自觉地承担起一个任务,就是以文学开启民智、教育民众,使他们有理性、有道德,共同构建一个完善、和谐的社会。与此相关的启蒙文学就有了两个特征:一是在内容上从歌颂上帝到写人,比如教育小说,就是写“人”的塑造成长,主人公在经历了种种的挫败和历练之后,终于成长为一个启蒙意义上的真正的人;另一个特征就是确立规范,这主要表现在戏剧方面。欧洲戏剧发达,而启蒙思想家都把戏剧看成是教育民众的工具。所以一时间戏剧大热。但当时德国的戏剧从剧本到演出都很混乱,没有一定之规,于是理论家高特舍特(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就从法国的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那里拿来“新古典主义”,写出了他的《写给德国人的批评诗学》。它首先是注重模仿,要求模仿古希腊、古罗马,强调结构的严谨、形式的完美,特别要求谨遵三一律,同时还要有明确、清晰、逻辑的语言。
高特舍特的理论给当时的文坛,特别是给混乱的德国戏剧制订了一个明确的规则,无疑是必要的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过分地苛求形式、规则,否定了想象和幻想,也就束缚了诗人的创造性。于是在启蒙队伍里的瑞士理论家布莱丁格(Johann Jakob Breitinger,1701—1776)和波德玛(Kohann Kakob Bodmer,1698—1783)与他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战,就是要肯定感情、想象等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们两人还研究德国中世纪的创作和民间文学,开始了文学的寻根。并认为,正是德意志民族的民间文学,而不是其他民族的文学,才是德国文学的根脉。波德玛还整理德意志的民间创作,编成他的《中古诗歌》,这是“民间”首次进入学者的视野。也正是承袭着这条线索,出现了“狂飙突进”运动。
在18世纪的德国,除了启蒙的科学理性的主旋律之外,还发育着一个情感文化。它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宗教的虔敬主义,另一个是世俗的感伤主义。虔敬主义是17世纪末兴起的新教中的一个派别,主张个人的、感性的宗教信仰。相对于路德的理性宗教,虔敬派更重视宗教的情感与心理因素,走的是重主观、重感情的实践性的心修之路。他们观照审视自己的内心,以自己的心直接去感觉体验上帝,让心灵与上帝直接晤对、交流,进而净化自己、提升自己,最终经历自我的重生,获得一个全新的存在。他们因与上帝相遇而感到幸福,因心灵与神明的沟通而心醉神迷,因获得上帝的宽恕而欣喜快慰。这是难以言说的个人神秘而神圣的宗教体验,而信仰和爱是其间的媒介。这些对以后浪漫派作家的宗教情结、对他们内心的情感体验和内心观照都影响极大,特别是对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和布伦塔诺。
与宗教性的虔敬感情相伴,18世纪还盛行世俗的情感至上的感伤主义。虔敬主义寻求心灵与上帝的交流,感伤主义则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友谊和爱情寻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感伤主义赋予启蒙文学一丝淡淡的伤感和脉脉温情。这在后期启蒙文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诗人艾瓦尔特·克莱斯特(Ewald Christina von Kleist,1715—1759)。席勒在他《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就认为,克莱斯特是首开感伤的诗人之一。而这些都成了浪漫派的远源,对海涅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狂飙突进”是18世纪60年代中到80年代在德国掀起的激进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歌德和席勒等市民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同于启蒙运动,“狂飙突进”没有系统的思想理论支撑,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的思想是其理论基础。与启蒙的理性相反,哈曼试图用直觉去说明信仰、道德和诗歌创作。“狂飙突进”有几个中心口号,如“个性”“自由”“天才”等,都标示出反抗与批判的精神。其锋芒所向,直指启蒙思想的核心:科学、理性与规则。它高扬天才的旗帜,认为天才是自然于人的最高体现,天才可以创造一切;它强调人的天性和本能:突出感性,崇尚自然。“狂飙突进”的代表人物认为,艺术不是技艺性的模仿,而是天才的创造,它出自一种理性不可解释的冲动,既不为主观意志所控制,也没有什么主旨,更不受任何人为规则的束缚,它只听从心的呼唤,它从天才的心中自然涌出,凝结而成为艺术。
赫尔德是“狂飙突进”的旗手,他撰写了大量的文艺批评,在批评中表达他的美学思想。赫尔德所处的时代,是启蒙中期,启蒙的科学理性在大展光辉之后,已经开始显露其局限。在文学领域就是多理性的逻辑,少形象的、感性的表达,具体到诗歌,还有重形式规则、少情感而导致的枯燥、生硬。赫尔德看到这些弊端,提倡一种自然而不做作、真实而不是拼凑、从心而出而不是从规矩而出的诗歌。
18世纪60年代欧洲出现了一个“莪相”热,莪相(Ossian)是传说中的古代爱尔兰说唱诗人,1758年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菲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声称发现了莪相,并完成了他诗作的英译《奥斯卡尔之死》(The Death of Oscar)。随后爱丁堡大学的教授休·布莱尔(Hugh Blair)1760年以匿名的形式将这个译本发表。并在1763年发表了关于莪相的文章,将其与荷马进行比较,并说明其区别。于是影响传播到欧洲大陆。莪相影响最大的是1765年的版本《莪相诗集》(The Poems of Ossian),其中收入了两首史诗和20首叙事抒情的歌谣,1768年出版了《迪尼斯》(Denis)的德译本第一卷(布伦塔诺就藏有这个版本)。事实上,这是些爱尔兰的盖尔人的诗歌,形成于12—15世纪,是民族和民间的产物。赫尔德正是看上了它的自然和真情实感,藉此阐述自己的思想[7]。他赞美那些“感性的、激情的、感情细腻的民间诗歌”,并且认为诗人也可以创作出具有这种精神的诗,比如荷马、莎士比亚和莪相。前提是回归自然,实现人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为这样的诗总结了几个“关键词”:“心灵的语言”(Sprache des Herzens)、“自然的精神”(Geist der Natur),以及感情的“直接”(unmittelbar)、“自发”(spontan)的表达等[8],这些都成了“狂飙突进”诗学的标志性的概念。与此相关赫尔德还提出了“民歌”(Volkslied)的概念,这是他仿照英语的popular song而创造的一个组合词,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与诗人的艺术的诗相对立,再就是对“民族”(Volk)及民族性的认可。
1765年英国人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s)出版了《古英语诗歌》(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这是英语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民谣集,反响很大,有感于英国人编英国民歌,赫尔德希望能有一位德国的珀西把自己的民歌结集出版,用淳朴清新的民歌来救正那些矫揉造作的诗,同时也想通过民歌的挖掘整理来建设德意志自己的文化,把一个分裂的民族从文化上整合起来。为此赫尔德亲自动手采集、征集民歌,并在1767年出版了《各族人民的声音》,其中收入了20首德语民歌。特别是他1773年出版的《德意志的风格和艺术》(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大力倡扬民歌,引起强烈反响,各种民歌集相继问世。同年毕尔格(Gottgried August Bürger,1747—1794)出版了 《雷诺拉》(Lenore)。1774年赫尔德出版《古代民歌》(Alte Volkslieder)。在前言中赫尔德说明自己的初衷,就是要通过民歌的收集整理,提倡一种自然的文学,并且特别提出整合发展德意志民族文学的愿望。1777年赫尔德又出版了《民歌》(Volkslieder),与此同时艾舍尔布尔格(Joh.Joachim Eschenburg,1743—1820)、尼古莱(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1733—1811)、艾尔维特(Anshelm Elwert,1761—1825)、格雷特(Friedrich David Gräter,1768—1830)、波特(Friedrich Heinrich Bohte,约1770—1855)等人也收集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民歌,这些日后都成了《号角》的底本。
赫尔德认为文学有民族性,所有的民族都通过歌唱表达自己的一切,包括认知、信仰、性格以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9]。因为各自社会生活的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风格[10],而德意志民族的风格是阳刚的、强健的[11]。他呼吁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包括德国人都去挖掘整理自己的文化遗产[12],并且问道,为什么总是希腊人?希腊人的歌、希腊人的画、希腊人的神话,“为什么不是我们?这里正召唤着德意志人”[13]。显然赫尔德有志于建立德意志民族的文学,而不是跟在其他民族后面亦步亦趋。更难能可贵的是,赫尔德对各民族持一种平等的态度,称其为兄弟,并没有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态度,他认为一个民族在一个更高的、人类一部分的意义上、自觉地认识自己的特点,这是一种爱国(patriotisch)。而抢救、保护民歌是为了认识自己和其他民族,也是为了诗歌今后的发展,因为它有借鉴的作用。正是出于这样的世界眼光和胸怀[14],他的民歌集《古代民歌》中也收入了其他民族的歌。总之,赫尔德在对生硬的理性规则的批判中建立了民歌理论。“民歌”伴随了他一生,对德语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受其沾溉的就是歌德。如果说赫尔德是民歌的理论家,那么歌德就是一个践行者。他接受了赫尔德的思想,1770年专门到斯特拉斯堡去追随他。他响应赫尔德的倡议,亲自到阿尔萨斯乡间去采集民歌,并将田野调查所得的14首口头流传的民歌交给赫尔德,编入了他的民歌集。歌德这期间写出的组诗《萨森海姆之歌》(Sesenheimer Lieder)明显受到了民歌的滋养,成为德语诗史上的洋溢着青春生命的华彩篇章。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就说过:“歌德很善于用比较独立的方式模仿民歌写过许多彼此风格极不相同的,较接近我们德国人情感的作品。”[15]
古典主义产生在18世纪80年代末,是歌德、席勒在“狂飙突进”之后面对社会和艺术现实重新进行反思的结果,是他们新的美学理想。它是在德国本土孕育成长的,与法国布瓦洛的古典主义不是一回事。它不是模仿的艺术,不是为宫廷服务的贵族艺术,而是积极乐观的、有社会进步理想的市民艺术。为区别彼此,德国文学史家称其为“魏玛古典主义”。
魏玛古典主义,既是美学理想,也是创作实践。基于古希腊艺术是人的艺术,是自然的艺术,古典主义反对简单的模仿,主张艺术建立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之上,建立在个人对艺术的感觉之上。它认为诗歌源自人的心灵、情感,同时又跟人生活的社会密不可分,因此艺术是人生的。古典主义不只关注文学,也关注人。相对于“狂飙突进”的自然人性,它主张道德的人性(sittliche Humalität)。出自泛神论的对人的内在神性的信仰,它认为人有天生的理想,有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内在要求。艺术既然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在人的心灵中占有一定的、不可替代的地位,那么艺术就可以是一种对人进行教育的手段,帮助人进行提升和完善。因此艺术的最终目的就不只是愉悦性情,它还能进行美育,提高人的道德,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美的心灵”在席勒看来,不仅是人性的客观最高阶段,也是人主观追求的幸福存在。显然,这是在启蒙理性与“狂飙突进”感性之间的调和。因此我们可以把启蒙运动、“狂飙突进”和古典主义三者的关系概括为,启蒙的理性是功利的,以合理、有益和利益为目的,古典主义的理性是人本的,要培养完善的人。而在人本这个层面上,“狂飙突进”强调的是自然天性,而古典主义则是道德的人性,突出的是美育,以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和谐。魏玛古典主义最辉煌的成就是歌德的诗剧《浮士德》。
就在古典主义兴盛的同时,浪漫派异军突起,它以颠覆启蒙和古典主义的面目出现,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文学史把它界定在1790到1850年间,并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它从文学入手,最后发展成一个波及全欧洲、影响整个19世纪的思想文化运动“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涵盖了文学、艺术、哲学、科学乃至政治诸领域,对整个西方思想史、艺术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它被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视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所经历的第三次转折[16],也是思想史上第一次发源于德国并向外“输出”,进而影响世界的思想文化运动。此前的德国一直是思想的“进口”国,人文主义以来的种种“运动”无不是从外国输入的。
浪漫派是一群比歌德、席勒小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他们大多家境优裕,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启蒙的摇篮里长大,但感觉到它的束缚,所以要冲破它,一展抱负。早期浪漫派(1790—1801)是一个聚在耶拿的朋友圈子,他们有大体一致的思想倾向、美学趣味,但没有统一的思想纲领,施勒格尔兄弟家的客厅就是他们的“基地”,奠定其美学理论基础的主要是弗·施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和诺瓦利斯,其哲学基础是康德和费希特的唯心论。施勒格尔指出:“这样一个时代,一言以蔽之,号称批判的时代。”[17] 它是由康德的三大批判开始的,从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角度对传统的一切重新进行审视,而浪漫派有自己的批判。他们看到科学、理性带来的人文缺失,于是构建起一个二元的“诗”的体系。首先是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超验的“诗”。《谈诗》中有:“所有艺术与科学最内在的奥秘属于诗。从那里生出一切,一切又必定回归那里。”[18] 即诗是万物之源,也是万物的归宿,于是诗也就成了本体。诺瓦利斯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
哲学通过它的规律给世界施加理念的影响时,诗通过自己特有与整体的联系而把握个体。如此诗就是哲学的锁钥、目的和意义。因为诗构建美丽的社会——世界大家庭——美好的宇宙……—因此诗就与生活连在一起。个人生活在整体里,整体体现在个体里。通过诗可以形成最高的互感与互动,它是有限与无限间最内在的统一。[19]
结合诺瓦利斯的其他著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思路:诗在诺瓦利斯那里高于哲学。它体现着无限和有限的统一,万事万物通过诗可以互动、互感,因此有限的人也可以感知无限的宇宙。诗还能构建从社会到世界到宇宙的美,于是它就在本体意义之外,又有了救世的功能。诺瓦利斯还说“诗是社会的基础”[20]。这样浪漫派就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滋养下,构建了自己超越艺术的、人文主义的“诗”,以及相关的“诗意”“诗意的人生”等别具含义的概念。其实质是通过“诗”,把人类提升到最高的境界,以实现对永恒、对绝对精神的追求。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就说过:“浪漫主义运动的特征总的来说,是用审美标准代替功利的标准。”[21] 由是形成了欧洲文化中独特的审美人文主义方向,即审美不只是单纯的艺术,而且有了关涉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可以说正是德国浪漫派奠立了这个方向的基石。
本体的诗之外,浪漫派对文学之诗也提出自己的观点:它是由诗人的灵性感知自己心底的“原初之诗”,“原初之诗”又激发诗人的想象,从而自然“流溢”而出的。弗·施勒格尔理想的诗“是无限的,是自由的,它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诗人随心所欲地不受任何约束”[22]。于是它要消解文学的形式,认为形式是束缚,而古典主义却XE"歌德"注重规则、注重形式美。再有浪漫派在哲学上强调“一”,就是在对立之后的“统一”“整一”,“一”是他们所追求的和谐与美。这点跟古典主义的理想相一致,但途径不同,它不是通过实践性的美育,而是要通过内在的心修在精神XE"精神"的层面来实现。在具体的创作上,浪漫派追求“融汇的诗”,就是一种融通了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的新的文学样式。弗·施勒格尔的《路琴德》是其代表。但总体说来,早期浪漫派的成就主要在理论建设,创作的成果并不多。
中期浪漫派(1801—1815)的代表人物是阿尔尼姆、布伦塔诺、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3;Wilhelm Grimm,1786—1859)、艾辛多夫等人。因为拿破仑对德意志的侵略和占领,中期浪漫派的思想明显地转向民族主义,他们试图通过对民族语言、历史、文学的整理研究推进民族教育,以对抗法国的影响。他们收集整理民歌、童话,不仅对保存民族文化居功甚伟,而且成就了各自的文学辉煌。晚期浪漫派(1820—1850)在思想上趋向天主教,成就主要在小说。如果在德国思想文化史的大坐标上看浪漫派,它是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进程中的一环,与之前的启蒙运动、感伤主义、“狂飙突进”、古典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大体说来,他们与启蒙和古典主义相远,与感伤主义、“狂飙突进”相近。
具体说到《号角》,它就是为建设民族文化,同时救正启蒙“却魅”的偏颇而编辑的。因为启蒙的理性把人类自童年以来的美好想象都视为迷信,把美丽的传说、民歌都视为糟粕而摒弃。浪漫派就是要重拾这些美好,构建一个德意志的“诗意的生活”。而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它接续了自人文主义以来的人文和审美的发展红线。
人文主义为它准备了14世纪以来的文本,而布伦塔诺对珍本、古本情有独钟,他自己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收藏。同时由人文主义者开始的建设德语的工作,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德语在18世纪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表现力丰富的语言,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也成为《号角》语言现代化的前提。而从启蒙时代开始,启蒙学者就萌生了文学寻根的想法,有了建立德意志民族文学的要求。到了“狂飙突进”,这种在启蒙时代被主调掩盖的声音就成了时代的主旋律。民歌成了民族文化的瑰宝,成了民族这棵大树的“根”,成了现实生活的鲜活呈现,也成了“文学”汲取营养的源泉。于是到了浪漫时期,建立民族的、纯粹审美的文学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拿破仑的侵略占领,更激发了民族和爱国的热情,于是《号角》就应运而生,它是一个总结,同时也是一个开启,开启了德语诗歌的新时代。如果说歌德的古典主义是以古希腊、罗马艺术为圭臬,那么浪漫主义特别是《号角》所开启的就是德意志的民族文学。这个新文学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础之上,体现着民族的风格和民族的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