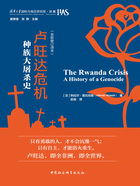
前殖民地时代卢旺达社会的神话与现实
我们初次观察卢旺达社会,要像第一批抵达卢旺达的欧洲人那样去“审视”。冯格岑(Von Götzen)及紧随其后的白人第一次抵达卢旺达后,就深刻地认识到了王权的力量。国王(mwami)居住在大型王宫的中央,是神一般的存在。国王是卢旺达的象征,其权力是神授予的,而不是世俗的。[24]比鲁(abiru)替国王精心操办各类程序繁琐的仪式,甚至国王的日常生活都要使用特殊的术语来表达,例如“口谕”(the King’s speech)、“御床”(the King’s bed)等。国王的权威也体现在名叫卡林加(Kalinga)的圣鼓上。没有人敲过这面鼓(可以敲打的是一些普通的鼓)。卡林加圣鼓装饰有敌人的睾丸。犯上作乱不但是重罪,而且也是渎神之举。国王是臣民之父、大家长,是伊玛纳(Imana,卢旺达人的上帝)委派给臣民的卢旺达之神、救世主。国王的统治完美无缺,绝无过错,其决定不容置疑。哪怕是没有受到国王公正对待的人,其父母也要向国王献礼,否则国王也会迁怒于受害者的父母,因为国王是迫不得已才给受害者父母带来不幸的。受害者父母仍然忠于国王,因为国王的处罚总是正确的。不管怎样,国王仍是尼亚加萨尼(Nyagasani),唯一的主,至高无上。[25]
但是,有几个欧洲人还是不满足于如此简单地理解卢旺达的王权特征,进而以斯皮克的早期“理论”来加以想象。其根本原因是,当时的欧洲人难以接受“完全未开化的黑人”在政治、宗教方面竟然发展到如此程度。欧洲人对于王权的想象还拓展至湖间地区其他大小王国[布干达(Buganda)、安科莱(Nkore)、布哈(Buha)、布希(Bushi)、布隆迪(Burundi)]及其国王。包括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爵士(后来成为英国驻乌干达总督)在内的探险家,提出一种王权理论:卢旺达的王权制度起源于埃塞俄比亚,起源于“游牧的入侵者”,而且契韦齐人(Bacwezi)的神话里还有关于“游牧的入侵者”的记忆。[26]由此可见,哈里·约翰斯顿是把斯皮克理论同19世纪末知识界的想象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卢旺达王权制度起源于“游牧的入侵者”的说法,也直接导致了图西人和胡图人的分化。当然,所谓“游牧的入侵者”,也就是图西人。图西人巧妙地征服了“低等”的胡图农民。这种观点后来成为殖民时代被普遍接受的“科学”真理。皮埃尔·里克曼(Pierre Ryckmans,20世纪20年代极其重要的比属殖民地总督之一)实事求是地归纳说:
图西人注定会占据统治地位。比起周围的低等种族,图西人相貌好,足以确立起极高的威信……胡图人,愚钝些,头脑简单、更知命些,也更轻信于人,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也从来不敢反抗。[27]
但是,国王处于复杂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的金字塔塔尖。一般而言,与所有传统社会一样,包括18世纪前的欧洲,卢旺达人的政治、文化、经济活动也深刻地纠缠在一起,无法区别开来。处于国王之下的是酋长(chiefs),酋长分为三种类型:[28]第一种是“管理土地的酋长”(mutwale wa buttaka),负责管理封地、农业生产、征税;第二种是“管理人的酋长”(mutawale wa ingabo),负责管理人口,包括替国王的军队招募士兵;第三种是“管理牧场的酋长”(mutwale wa inka或mutwale wa igikingi),负责管理牧场。如果某个地区是稳定的,酋长可能会身兼三职;如果某个地区有反叛活动或反叛倾向,国王就会根据“分而治之”原则,选任三个酋长分管三职。胡图人主要就是种地的,因此很多“管理土地的酋长”是胡图人。即便如此,绝大多数酋长仍是图西人。为了使事情变得复杂(此乃国王所乐见),A酋长可能既是某一个山头“管理人口的酋长”和“管理牧场的酋长”,但这个山头还有另一个“管理牧场的酋长”(B酋长),与A酋长形成竞争关系。同时,A酋长也可能是其他多个山头的“管理人口的酋长”,但其他权力则为第三方(C、D等)酋长所享有。德国第一任驻卢旺达特派代表理查德·坎特(Richard Kandt),妙称之为“缠手指”(the intertwined fingers)制度。
与卢旺达所有政府官员一样,酋长有两个基本功能:社会控制与经济剥削。社会控制手段多种多样;在接近王国中央的区域,社会控制非常严厉;地区越偏远,社会控制也就越松弛。经济剥削有好几种形式,主要体现为三项劳动:维护酋长的院落(kwubaka inkike)、土地耕作(gufata igihe)、照看牛群(ubushumba bw’inka)。但是,这三项劳动也不完全算是经济剥削,劳动者也会获得某种形式的“工资”。[29]无论是各种义务还是赋税(以实物形式缴纳),并非分散到每个人的头上。酋长为其管辖下的山头制定统一的劳动/支付办法,山头上的每户人家自行安排,以满足政府的需求。[30]后来,比利时人过分强化原来的赋税制度,并用欧洲赋税制度取代非洲人更加温和的共同承担赋税的方式,强制要求每个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纳税。卢旺达人对此抱怨不迭。19世纪末,卢旺达新引入一种名为乌布雷特瓦(ubuletwa)的劳役制度,卢旺达农民在此之前闻所未闻。[31]这一劳役制度要求卢旺达人为“公共利益”提供劳动。19世纪末,为了扩展统治范围,国王鲁瓦布吉里(Rwabugiri)大力推广乌布雷特瓦劳役制度。后来,乌布雷特瓦劳役制度成为卢旺达各地抵抗集权压迫的标靶。比利时殖民者非常偏爱并滥用乌布雷特瓦劳役制度。比起传统赋税制度,卢旺达人对乌布雷特瓦劳役制度更加不满。
然而,乌布哈克制度(ubuhake)才是反映卢旺达社会个人依附关系的典型制度,引发世人极大的关注和争议。无论卢旺达人还是外国人,都对乌布哈克制度有不同理解。1959年的暴力活动,彻底把卢旺达人分化为两个互相敌视的社会群体:图西人和胡图人。此后,图西人和胡图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乌布哈克制度。图西人认为,乌布哈克制度是一种温和的制度,充满善意,不同家族借此可以形成一种友好互助的契约关系。胡图人认为,乌布哈克制度是一种苛刻的制度,带有奴役意味,图西主子借此可以剥削贫穷的、受压迫的胡图人。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32]说到底,乌布哈克制度是一种不平等的契约关系,涉及两个群体:庇护人(shebuja)和受庇护人(mugaragu)。在一种典型的乌布哈克制度的表现形式(可能不是乌布哈克制度最初的表现形式)中,图西庇护人会给胡图受庇护人一头母牛。但是,这头母牛只是一种财富、权力的象征,胡图受庇护人在理论上并没有这头母牛的所有权。这头母牛不但是胡图受庇护人的一个“经济上的”礼物,而且也是胡图受庇护人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母牛可能会下崽,未来的小牛犊将是庇护人、受庇护人所共有的,进而成为胡图受庇护人向上层社会攀爬的起点。一旦胡图人拥有牛,其家族[33]就成为“去胡图化”的人(icyihuture),即一半是胡图人,一半是图西人。[34]当然,拥有牛的胡图家族还是非常依赖图西庇护人的:一些图西庇护人极其吝啬,贫穷的胡图受庇护人要为图西庇护人承担许多义务性劳动,压根不可能摆脱图西庇护人的掌控。
总的来说,乌布哈克制度其实最初并不是图西人与胡图人之间,而是两个图西家族之间的制度。[35]一旦成为两个群体之间而非单一群体内的契约,乌布哈克制度的形式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例如,在乌布哈克制度没有推广之前,“禁牛令”(禁止胡图人养牛)执行得并不太严格。胡图人所拥有的牛只,通常也只是因作战勇敢而获得的奖励。胡图人可以把牛只作为私人财产,无需向主子履行社会义务。前殖民地时代,卢旺达经常爆发战争。战争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抵御外敌,保卫王国;二,征服其他地区,扩疆拓土;三,抢夺邻近部落的牛群。马凯(Maquet)的观点并不对,[36]作战的并非只有图西人,所有卢旺达群体都加入军团(intore),地位低下的特瓦人还因作战勇敢而备受赞赏。每个卢旺达军团都有名号,通常还比较浮夸,如“硬汉团”(abashkamba)、“第一荣誉团”(imbanzamihigo)、“无畏团”(inzirabwoba)等等。很多战斗,尤其是同敌对王国的战斗,几乎就是一场仪式表演,士兵一对一决斗。因此,德拉热尔称“卢旺达军团作战时具有堂吉诃德式特点”,还说伟大的征服者基盖里四世(Kigeri Ⅳ)鲁瓦布吉里(1853—1895)在战场上持重谨慎,且鲁瓦布吉里更愿意大量招募胡图人,胡图人形貌可能不太体面,但其战斗力更强。[37]
战争是“社会凝结剂”,尽管图西人、胡图人、特瓦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但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毕竟又都是卢旺达人。此外,宗教也是社会团结的另一根纽带。卢旺达和湖间地区其他王国都有传统宗教,名曰库班杜瓦(kubandwa)。[38]按照字面意思,虔诚的库班杜瓦信徒(imandwa)也就是“遭到抢夺的人”,而抢夺库班杜瓦信徒的正是万神之主卢杨贡贝(Ryangombe),也正是卢杨冈贝把库班杜瓦彻底转变为一种带有邪教性质的宗教信仰。[39]与其他诸如此类的信仰一样,可能起源于胡图人的库班杜瓦也被卢旺达人广泛接受。库班杜瓦虽然不太欢迎图西人参加其宗教仪式,但卢旺达社会的三个群体都有其信徒。
在碎片化的社会里,氏族是社会群体分类的基本手段。奇怪的是,氏族在卢旺达却没有这种功能。家庭、家族(umuryango)究竟是图西人,还是胡图人,[40]并不取决于氏族(ubwoko)。卢旺达氏族既有图西人又有胡图人,甚至还有特瓦人。所谓“氏族”,名不副实,因为卢旺达氏族没有关于某个共同祖先的记忆,甚至也没有关于某个共同祖先的传说。[41]就此而言,我们需要重视戴维·纽布里(David Newbury)的观点。纽布里认为,氏族其实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随着卢旺达国王把自己的统治慢慢扩展至原先处于独立状态的地区,所谓“氏族”就取代了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真正”氏族。[42]
以上内容主要是静态描述,下面我们将论述动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