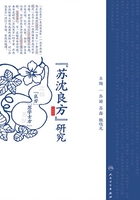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二、沈括的医学思想与贡献
沈括作为一个“博通物理”的自然科学家,一个认真严谨的医学研究者,本着“亲验有效”的原则搜集整理了《良方》一书,书中表现出沈括独特的医学思想。
(一)“万物皆主于气”的整体思维
沈括的医学观继承了朴素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思想。中国古代哲学“气一元论”学说认为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宇宙万物的存在形式有两种:一曰“有形”,即有形状的具体实物;二曰“无形”,或称“虚空”。“虚空”即“气”,广阔无垠的宇宙“虚空”充满着“气”。天地自然万物,无论是有着具体形态的实物,抑或实物之间看不见、摸不着的“虚空”,皆由“气”构成,都充满着“气”,所不同的只是构成实物的气为“聚合”状态,构成“虚空”之气呈“弥散”状态。《黄帝内经》承袭了“气一元论”学说,并在“人体之气”与“天地自然之气”的相互感应交换上有所发挥:“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时立气布,如环无端,候亦同法。” 1沈括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气”的变化表现形式,即“凡积月以为时,四时以成岁,阴阳消长,万物生杀变化之节,皆主于气而已” 2。大到宇宙天体,小到人体,都是“气”所构成的,都与“自然之气”相通,这是中医“气一元论”整体思维的表现。沈括说:“日月,气也,有形而无质。故相值而无碍。” 3他肯定日月都是“气”构成的,认为“气”没有形状,所以运行时相遇而不相妨碍。
1 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62-66.
2(宋)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50.
3(宋)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60.
沈括认为运气所主导的是事物变化之常理,但变化无所不至而各有征兆,随着这些变化,各种流行病相应发生,对应的方法不尽相同。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出:“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 4这里说的是自古医家有“五运”的计算之术,大的方面如推断天地变化、寒暑风雨、水旱虫灾都有一定的规则,小的方面如人的各种疾病也随着气运而盛衰变动。后世的人不了解它的作用,拘泥于死板的套路,所以其精妙的运算都没有很好地应验。举例来说,如果厥阴木运占主导地位,它的气多风,民众患腹泻病,难道普天之下都是多风、天下民众都患腹泻病吗?乃至于在同一城邑而晴雨也有不同的,气运之说也要全面考虑。大体来说,事物运动有常理、有变化,运气所主导的是常理,不同于运气所主导的都是变化,常理遵循本气,变化则无所不至而各有征兆,所以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的变化,对应的方法都不相同。随着这些变化,各种流行病相应发生,都根据当时、当地的征候,即使在几里之内,只要气候不同,相应的现象全都不同,不能拘泥于死板套路 1。
4(宋)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61.
1(宋)沈括.梦溪笔谈全译[M].金良年,胡小静,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71.
沈括对医家之“五运六气”评价甚高,认为它有准确预测岁时疾病的作用。其一是因为他自己思想上继承了“气一元论”宇宙观,就对同样建立在“气一元论”基础上的《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说特别认同;其二是因为他曾担任过北宋司天监主管,并主持修纂了《奉元历》,因而对历法推算和天文观察记录独具匠心。沈括晚年还提出了《十二气历》,可以说从科学家的角度高度赞扬印证了“五运六气”的医学价值,只是世人甚少精通历法,所以未能完全参悟其中的精妙。沈括在《良方》原序中进一步强调“五运六气”是人体致病的重要因素,医家不可以不仔细辨察,“古以治疾者,先知阴阳运历之变故,山林川泽之窍发,而又视其人老少肥瘠,贵贱居养,性术好恶,忧喜劳逸,顺其所宜,违其所不宜。……五运六气,冬寒夏暑,  雨电雹,鬼灵魇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负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强弱,五脏异禀,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形彼,亦不以一人例众人,此人事也。言不能传之于书,亦不能喻之于口”。近世很多医家仅仅参考方书上的现成药方,不去辨证而勉强套用,仅一二味药符合症状就直接开给病人,最多不过叮嘱一下服药方法和注意事项就完事了,不会考虑到“上天五运六气”与“山林川泽之气”对人体脏腑病变的影响,也不会结合病人个体差异,因而治愈率不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沈括建立在“气一元论”基础上的中医整体思维与辨证施治的理念。
雨电雹,鬼灵魇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负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强弱,五脏异禀,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形彼,亦不以一人例众人,此人事也。言不能传之于书,亦不能喻之于口”。近世很多医家仅仅参考方书上的现成药方,不去辨证而勉强套用,仅一二味药符合症状就直接开给病人,最多不过叮嘱一下服药方法和注意事项就完事了,不会考虑到“上天五运六气”与“山林川泽之气”对人体脏腑病变的影响,也不会结合病人个体差异,因而治愈率不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沈括建立在“气一元论”基础上的中医整体思维与辨证施治的理念。
 雨电雹,鬼灵魇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负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强弱,五脏异禀,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形彼,亦不以一人例众人,此人事也。言不能传之于书,亦不能喻之于口”。近世很多医家仅仅参考方书上的现成药方,不去辨证而勉强套用,仅一二味药符合症状就直接开给病人,最多不过叮嘱一下服药方法和注意事项就完事了,不会考虑到“上天五运六气”与“山林川泽之气”对人体脏腑病变的影响,也不会结合病人个体差异,因而治愈率不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沈括建立在“气一元论”基础上的中医整体思维与辨证施治的理念。
雨电雹,鬼灵魇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负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强弱,五脏异禀,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形彼,亦不以一人例众人,此人事也。言不能传之于书,亦不能喻之于口”。近世很多医家仅仅参考方书上的现成药方,不去辨证而勉强套用,仅一二味药符合症状就直接开给病人,最多不过叮嘱一下服药方法和注意事项就完事了,不会考虑到“上天五运六气”与“山林川泽之气”对人体脏腑病变的影响,也不会结合病人个体差异,因而治愈率不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沈括建立在“气一元论”基础上的中医整体思维与辨证施治的理念。
沈括用医药学的自然科学知识,论证物质是由“气”构成的。如《苏沈内翰良方·论脏腑》提到:“五脏之含气呼吸,正如冶家鼓鞴。人之饮食药饵,但自咽入肠胃,何尝至五脏。凡人肌骨、五脏、肠胃虽各别,其入腹之物,英精之气,皆能洞达,但滓秽即入二肠。凡人饮食及服药,既入腹,为真气所蒸。英精之气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细研硫黄、朱砂、乳石之类,凡能飞走融结者,皆随真气洞达肌骨,犹如天地之气贯穿金石土木,曾无留碍,其余顽石草木,则但气味洞达尔。及其势尽,则滓秽传于大肠,润湿入小肠,此皆败物,不能变化,惟当退泄耳。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尔,凡质岂能到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人体摄入饮食水谷和药饵经过五脏气化,其精华被人体吸收,糟粕入大、小二肠,所谓某药入某脏并非是真的有形物质到达该脏器,而是气味精华到达而已,正如“天地之气”可以贯穿“金石土木”,也可以弥散于“顽石草木”间。这段话既是对“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点合乎科学的说明和论证,更是值得医家学习的至臻见解。沈括还在《梦溪笔谈》中引用《黄帝内经》原文,论述他自己的“五行”思想。“《洪范》‘五行’数,自一至五……唯《黄帝素问》:‘土生数五,成数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无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画而为图,其理可见。为之图者,设木于东,设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为生数,各并中央之土,以为成数。土自居其位,更无所并,自然止有五数,盖土不须更待土而成也。” 1他坚持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把“五行”看成神秘莫测的东西,而是看成物质的自然现象。正如《良方》原序所言:“疾发于五脏,则五色为之应,五声为之变,五味为之偏,十一脉为之动,求之如此其详,然而犹惧失之。此辨疾之难一也。”如果疾病在人体五脏发生,那么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声(呼、笑、歌、哭、呻)、五味(酸、苦、甘、辛、咸)等就会表现出对应不同脏腑的病变之象。也就是说,人体的病变总不是孤立的,因为“五脏之气”与“天地之气”相通。而“五行”也不是完全虚无的概念,它既可以对应具体的“声色形貌”,也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论。
1(宋)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56.
(二)辨证施治理念
中医最具代表性的思维模式是辨证施治理念。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是根据病人的叙述,抓住一两条病症就轻易下结论;更不是见什么病症就套用什么药方。辨证施治通过望、闻、问、切等多种途径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病症,仔细分析病因病机,找出主要致病因素,集中针对主要矛盾采取相应措施,并同时兼顾对病人整个身体的调节。这是中医诊疗的精髓,也是中医整体思维优于西医解构思维的地方。
《良方》中记录有许多沈括运用辨证施治理念进行科学救治的病例。如《苏沈内翰良方·论君臣》记载:“所谓君者,主此一方,固无定物也。《药性论》乃以众药之和厚者定为君,其次为臣、为佐,有毒者多为使,此谬论也。设若欲攻坚积,则巴豆辈岂得不为君也?”他认为在药方中没有绝对固定的所谓“君、臣、佐、使”,什么药应该为“君”应当辨证来看。像《药性论》中所说,在众多的药物中,“和厚者”当为“君”,次者为“臣”或为“佐”,有毒的药物只能是“使”,这是荒谬的言论。比如治疗攻克顽固积滞类的疾病,怎么能不用巴豆一类攻坚性强的药作为“君”药使用呢?旧时古方中所说的“一君,二臣,三佐,四使”,其用意是说治疗疾病可供使用的药物虽多,但是主治病症一般专在一种药物才能正中靶心,其他药物只是用来辅助主药发挥作用的,而且一方中的各个药物之间可以相互促进激活,使药方发挥最大效用。施治者需当懂得辨证的思想,才能正确领悟古方的奥妙,否则就会沦为庸医只会开一大堆药,却找不到主要致病因素,也使药物发挥不了作用。沈括虽然不是以行医为生,却比很多医生更能领会中医整体观和辨证施治的精髓。
沈括非常强调辨证施治,再好的药方也有对应的主治之证,不能以一概全。如《苏沈内翰良方·小柴胡汤》说:“近岁此药大行,患伤寒不问阴阳表里,皆令服之,此甚误也。此药《伤寒论》虽主数十证,大要其间有五证最的当,服之必愈……其余证候,须仔细详方论及脉候相当方可用,不可一概轻用。世人但知小柴胡治伤寒,不问何证便服之,不徒无效,兼有所害,缘此药差寒故也。唯此五证,的不蹉跌,决效无疑,此伤寒中最要药也。家家有本,但恐用之不审详,今备论于此,使人了然易晓。”本段文字是对张仲景《伤寒论》中小柴胡汤的临床应用说明。他详细列举了本方适用的五大证候:身热,心中逆或呕吐者;寒者,寒热往来者;发潮热者;心烦胁下满,或渴或不渴者;伤寒已瘥后,更发热者。他还指出除上述所列五大适用证候外,其余证候要仔细对照方论并检查脉候,两相对应才可使用。沈括说小柴胡汤虽然是治疗伤寒有代表性的名方,几乎家家必备,人手一方,但是却有乱用的现象,奉劝世人决不能只要是伤寒,也不问阴阳表里虚实,不辨证就服小柴胡汤,这样做不但不能治病,还危害匪浅。
沈括告诫人们治病不能尽信方书,一定要仔细辩证。如《苏沈内翰良方·茯苓散》曰:“方书言梦泄,皆云肾虚,但补肾涩精,然亦未尝有验……医及摄生家多言,梦寐甚于房劳,此殆不然。予尝验之,人之病,天行未复,而犯房劳者多死,至于梦寐,则未尝致困,此决然可知,但梦寐自有轻重耳。”据方书所言,梦遗梦泄都是因为肾虚,治法就是补肾涩精,但是往往服了药也没什么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沈括意识到治疗梦泄同样是需要辨证的,也不能依古书照本宣科,以一应百。他从自己治疗的经验出发总结出梦泄的三种症状:一种比较严重,是至虚之证,乃肾虚不能统摄精气,从而心不能控制意念,有在梦中而泄的,也有不梦而泄的,这是比较严重的症状,需要服大量的补药来调理,但是一般得这种病症的人非常少。多数人不过是阴虚烦热而已,因心有所想,所以梦中遗泄,这种证候很容易治疗,只要服用茯苓散一段时间,便能自愈,且沈括用此方医治病人都非常见效。还有一种属于少年人气血旺盛,或者是禁欲已久的鳏夫及道士,因为长期强行抑制情欲,偶有所感而导致遗泄,这种属于正常现象,不算是病。沈括通过对这三种证候的辨证分析来说明多数梦遗之症其实并不严重,更不像道家养生书上所说的梦遗比房事还会导致人虚劳。我们经常看到房事频繁致人虚劳而死的,但是很少听说梦遗会导致死亡的,可见方书不可尽信。
除了论述治疗疾病讲究辨证施治外,沈括在药物的采摘时机上也特别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沈括敢于批驳历代本草书籍中记录的惯用做法。如《苏沈内翰良方·论采药》云:“古方采草药,多用二八月,此殊未当。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辨识耳,在药则未良。”沈括提出二月、八月采药未必是该药物的最佳采摘时机,古方之所以这样记载是因为根据时令一般本草在二月时已经发芽,八月时又尚未枯萎,这个时候的本草特征比较明显,容易辨认。但这时期采摘的本草却未必是药效的最佳时期,应该根据用药部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对于需要用根的本草来说,如果其有宿根,则应该选取没有长茎叶的时候采摘,这样本草的营养就会全都聚集在根部,这样的根用起来药效自然更好。沈括还进一步用生活中常见的本草来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有不相信自己的说法想要查验的人,可以观察萝卜、地黄一类用根的本草,在没长苗的时候采摘,它们的根大且充实饱满;在有苗的时候采摘,它们的根就轻飘虚浮。对于那些没有老根的用根药物,要等到苗已经长成但是尚未开花的时候采摘,那么它的根已经长结实但却又没太老,例如像紫草一类的药物,在还没开花时采,它的根颜色鲜亮;在已经开过花后再采摘,它的根就颜色暗淡。对于用其叶子和嫩芽的本草,就在叶子或芽刚刚长成时采摘;对于用其花的本草,就选取花刚开的时候采摘;对于用其果实的本草,就选取果实刚刚成熟的时候采摘,这些都不可以用固定的时月来限制,否则采集的本草就达不到最理想的药效。这是因为各地的地气有早有晚,天时变化也不总是相同,时令到达的实际时间就不一样。所谓地气,也就是一年四季太阳光照大地带来相应的热量,大地上的动物、植物感受热量变化所对应的物候表现;或者因为地理海拔的不同,土地感受太阳热量先后的区别,比如平地如果三月开的花,深山中可能四月才开花。正像白居易游大林寺时所作的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正开。”这是因为地势高低不同造成的时令有先有后,这本来是很寻常的道理。又比如竹笋和稻米就有成熟时间早晚不同之区别,吴越地区的桃李夏天结出果实,朔北大漠的桃李夏天则只能开花,这都是因为地气的不同造成的。还有同亩上的庄稼,因为灌溉和肥料施给的不同也有长势不同的区别;同一个丘田上的禾苗也有因为耕种的早晚而收获时间不同,这些是属于人力的因素造成的,都不能一概而论。沈括用庄稼、果实这些常见的作物来举例说明,这些常见作物尚且需要考虑天时、地理、人力因素的不同而区别耕种和收获,更何况是用来挽救人生命的本草药物呢?从而得出本草书籍中记载的药物采摘时间一刀切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应该根据用药部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而且也应该把天时、地理、人为等因素考虑进去。
沈括还提出煮药的细节差别也会影响患者服药的效果。《良方》原序云:“古之饮药者,煮炼有节,饮啜有宜。”沈括认为有的药需要久煮,有的药不能久煮;有的药适合用大火猛煮,有的药适合用文火慢熬;有的药适合热饮,有的药适合冷啜;有的药适合快速一饮而尽,有的药需要缓缓摄入;有的药适合高兴或生气时服用,情志能够激发药效,有的药服用时要尽量避免太过高兴或生气,以免影响药效发挥。即使是煎药用流水和止水的不同、水质清浊的不同、矿物质含量的不同等等,都会导致药效的区别,更何况是还有人为的作用,勤恳的煎药者能够按说明仔细操作,而懒惰的就敷衍了事。这些细节的差别都可能影响患者服药的效果,如果病人不去考虑以上影响药效发挥的诸多因素,就会一味指责医生开药没有效果。因此,作为医生更要格外小心谨慎,除了一定要对症用药外,考虑问题还要细致周到。
(三)科学求真思想
沈括特别重视亲身实践、调查与研究。他会用敏锐的科学眼光捕捉那些真假参半的谬说传闻,仔细观察,反复研究,去伪存真,保留有科学价值的信息,并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其中的科学道理。沈括在《良方》原序中表明了自己致力于收集良方的原因及原则:“世之为方者,称其治效,尝喜过实,《千金》《肘后》之类,犹多溢言,使人不敢复信。予所谓《良方》者,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闻不预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谓五难者,方岂能必良哉!一睹其验,即谓之良,殆不异乎刻舟以求遗剑者?予所以详著其状于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几偶值云尔。”沈括认为现在世上流传的所谓良方,大都夸大效验,有言过其实之嫌,尤其是像《备急千金要方》《肘后备急方》等医书中收录的药方,经常使用夸赞溢美之词,其效果却往往差强人意,使人不敢再轻易相信。而这正是沈括自己收集效验良方的原因。他收集良方的主要原则就是一定要眼见为实,要自己亲自目睹过其治疗效果或亲自试用过才会收录,如果只是听说过而没有验证过的药方是不会收录的。并且他一再强调对疾病的审查要非常谨慎仔细,考察多种因素,所谓良方应该辨证施治,没有一概而论的,因此他在每一个药方后面都会详细记录该方所对应的病证、药方来源、具体用药方法等,期许有恰好碰到类似病症的人试用此方能够见效。他的这种录方的方法也被后世视为开“本事方”之先河,由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沈括的医者仁心与谨慎对待疾病的科学求真思想。沈括在《良方》收集的很多药方中常有“予家常作此药”“予自得此,治疾无有不效”“用此药法,遂永瘥”“予目见医数人”等字眼,记录了很多沈括自己及家人患过,或他亲自救治过的疾病,且使用的药物多为常见易得,方法多是简便易行,足见其不是亲验有效则不予收录的务实原则,这也正是沈括不求虚名夸赞,但求科学求真的体现。
沈括的科学求真思想还体现在《良方》收录的很多医论中。如《苏沈内翰良方·论脏腑》记载:“如枇杷、狗脊,毛皆不可食,食之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论甚多,皆谬说也。又言人有水喉、食喉、气喉者,谬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水与食同嚼而吞,岂能口中遂分二喉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则纳饮食,喉则通气。”沈括提出古方及世俗言论中总有一些荒谬不可尽信的地方,比如认为枇杷、狗脊一类食物的毛不能吃,吃了就会进入肝肺不能去除,这些都属于无稽之谈。还有的认为人有三个喉管,即水喉、食喉、气喉,这也是谬说,而现世流传的《欧希范真五脏图》,即广西少数民族首领欧希范率部起义遭镇压杀戮后,由医官所绘其人体五脏解剖图也画了三喉,这个错误大概是因为当时没有认真审查造成的。沈括进一步解释三喉说的荒谬:水和食物一同经过人的口腔咀嚼吞咽,怎么能在口中分为两个喉管输送入体内呢?人应该只有两个喉管而已,一个是咽,主要是吸纳饮食的功能,水谷是不能分开的;另一个是喉,主要是通气的功能。这个见解敢于否定古书和官绘的人体五脏图的错误,表现了沈括敢于否定权威,实事求是的科学求真思想,并且用浅显的语言解释其中的科学道理,纠正方书及世俗所传谬误,让人信服。
沈括在科学求真思想的指导下,还纠正了本草书籍中的很多错误。在《笔谈》卷二十六及《补笔谈》中都有“药议”章节,是对一些本草的考证内容,且这些本草考证议论部分也收入了《良方》之中。如《苏沈内翰良方·论鸡舌香》云:“按《齐民要术》:鸡舌香,世以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华子》云:鸡舌香治口气。所以三省故事,郎官含鸡舌香,欲其奏事对答,气芬芳,此正谓丁香治口气,至今方书为然。又古方五香连翘汤用鸡舌香,《千金》五香连翘汤,无鸡舌香,却有丁香,此最为明验。新补《本草》又出丁香一条,盖不曾深考也。今世所谓鸡舌香者,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剖开中如柿核,略无气味,以此治疾,殊极乖谬。”在这部分考证内容中沈括指出古方时而称“丁香”,时而称“鸡舌香”,实则是一物,因为“鸡舌香”外形似丁子,所以又名“丁子香”即“丁香”,有香口之功效。古方与《千金方》中就有同方异药名的记载,证明“丁香”就是“鸡子香”。当时新编的《嘉  补注本草》中除“鸡子香”外又单出“丁香”一条,这是因为没有进行深入考证,而当时世上所用“丁香”都是从“乳香”中得到,其外形和气味都和古方书中记载的不符合,如果以此治疗古方书中对应的疾病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错误。又如《苏沈内翰良方·论甘草》云:“《本草注》引《尔雅》云:
补注本草》中除“鸡子香”外又单出“丁香”一条,这是因为没有进行深入考证,而当时世上所用“丁香”都是从“乳香”中得到,其外形和气味都和古方书中记载的不符合,如果以此治疗古方书中对应的疾病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错误。又如《苏沈内翰良方·论甘草》云:“《本草注》引《尔雅》云:  ,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叶似荷,青黄色,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故谓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生如相思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则角拆。子如小扁豆,极坚,齿啮不破。”沈括对比甘草和《本草注》中所描述“
,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叶似荷,青黄色,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故谓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生如相思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则角拆。子如小扁豆,极坚,齿啮不破。”沈括对比甘草和《本草注》中所描述“  ”的外形极为不符,前者高五六尺,枝叶都和槐树类似;后者是蔓生,叶似荷。又根据其味极苦,所以判定“
”的外形极为不符,前者高五六尺,枝叶都和槐树类似;后者是蔓生,叶似荷。又根据其味极苦,所以判定“  ”应该是“黄药”,从而也解释了“大苦”之名的由来。沈括提出“
”应该是“黄药”,从而也解释了“大苦”之名的由来。沈括提出“  ”在《尔雅》郭璞注为“甘草”是错误的,由于《尔雅》是古代经学必读书目,具有学术权威的指导性,于是这个错误就被历代本草书籍所沿用。他这种敢于向古代学术权威挑战的科学求真精神在经学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实在难能可贵。由此,沈括的科学求真思想还体现在他对药物反复的科学考证,对古代方书和本草书籍去伪存真。他认为医生用药应该非常谨慎,不能因为没有经过全面考证就尽信本草书籍的记载,如果名实不符用错了药,将会关乎人命安危,这是医生最该警醒的以“人命为先”的科学求真思想。
”在《尔雅》郭璞注为“甘草”是错误的,由于《尔雅》是古代经学必读书目,具有学术权威的指导性,于是这个错误就被历代本草书籍所沿用。他这种敢于向古代学术权威挑战的科学求真精神在经学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实在难能可贵。由此,沈括的科学求真思想还体现在他对药物反复的科学考证,对古代方书和本草书籍去伪存真。他认为医生用药应该非常谨慎,不能因为没有经过全面考证就尽信本草书籍的记载,如果名实不符用错了药,将会关乎人命安危,这是医生最该警醒的以“人命为先”的科学求真思想。
 补注本草》中除“鸡子香”外又单出“丁香”一条,这是因为没有进行深入考证,而当时世上所用“丁香”都是从“乳香”中得到,其外形和气味都和古方书中记载的不符合,如果以此治疗古方书中对应的疾病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错误。又如《苏沈内翰良方·论甘草》云:“《本草注》引《尔雅》云:
补注本草》中除“鸡子香”外又单出“丁香”一条,这是因为没有进行深入考证,而当时世上所用“丁香”都是从“乳香”中得到,其外形和气味都和古方书中记载的不符合,如果以此治疗古方书中对应的疾病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错误。又如《苏沈内翰良方·论甘草》云:“《本草注》引《尔雅》云:  ,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叶似荷,青黄色,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故谓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生如相思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则角拆。子如小扁豆,极坚,齿啮不破。”沈括对比甘草和《本草注》中所描述“
,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叶似荷,青黄色,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故谓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生如相思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则角拆。子如小扁豆,极坚,齿啮不破。”沈括对比甘草和《本草注》中所描述“  ”的外形极为不符,前者高五六尺,枝叶都和槐树类似;后者是蔓生,叶似荷。又根据其味极苦,所以判定“
”的外形极为不符,前者高五六尺,枝叶都和槐树类似;后者是蔓生,叶似荷。又根据其味极苦,所以判定“  ”应该是“黄药”,从而也解释了“大苦”之名的由来。沈括提出“
”应该是“黄药”,从而也解释了“大苦”之名的由来。沈括提出“  ”在《尔雅》郭璞注为“甘草”是错误的,由于《尔雅》是古代经学必读书目,具有学术权威的指导性,于是这个错误就被历代本草书籍所沿用。他这种敢于向古代学术权威挑战的科学求真精神在经学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实在难能可贵。由此,沈括的科学求真思想还体现在他对药物反复的科学考证,对古代方书和本草书籍去伪存真。他认为医生用药应该非常谨慎,不能因为没有经过全面考证就尽信本草书籍的记载,如果名实不符用错了药,将会关乎人命安危,这是医生最该警醒的以“人命为先”的科学求真思想。
”在《尔雅》郭璞注为“甘草”是错误的,由于《尔雅》是古代经学必读书目,具有学术权威的指导性,于是这个错误就被历代本草书籍所沿用。他这种敢于向古代学术权威挑战的科学求真精神在经学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实在难能可贵。由此,沈括的科学求真思想还体现在他对药物反复的科学考证,对古代方书和本草书籍去伪存真。他认为医生用药应该非常谨慎,不能因为没有经过全面考证就尽信本草书籍的记载,如果名实不符用错了药,将会关乎人命安危,这是医生最该警醒的以“人命为先”的科学求真思想。
综上所述,沈括不但在《良方》中体现了整体思维、辨证施治、科学求真等医学思想,还注意药物与文献的对应,综合考证古书的记载,参照自己的实际考察,纠正了本草书籍中收录的多处错误。沈括严谨的科学精神使他形成了对医学独特的研究领悟,对每一药方所对应的病症、用药注意事项、亲自实践的治疗心得等均做了详细记录,这些记录具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