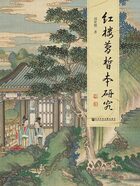
第七节 他叫“方春”,还是叫“方椿”?
皙本独异的人名,最后一个便是方春。
他是一位花儿匠,出现于第24回。
贾芸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向凤姐进贡了冰片、麝香,终于谋得一个在大观园种植花木的差事,领到了二百两银子,还了醉金刚倪二的借款。于是:
这里贾芸又拿了五十两,出西门,找到花儿匠方春家去买树。
方春之名,全书仅在这里出现一次,却有着异文。
上述三句引文,彼本仅作“这里贾芸又去买树”一句,躲开了花儿匠“方春”之名。彼本与皙本关系比较亲近,不知它为何做这样的删节。如果不删节,不知此处是否也会出现此花儿匠之名。如果出现花儿匠之名,不知是否和皙本一样,也作“方春”。
在其他脂本(庚辰本、舒本、杨本、蒙本、戚本、梦本)中,“方春”均作“方椿”。
面临“春”“椿”二字的歧异,我们该如何抉择与剖析?
我认为,此人之名应以“椿”为是,以“椿”为优。
“椿”即椿树,一种落叶乔木。古人传说大椿长寿。《庄子·逍遥游》云: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后世因以“椿年”“椿龄”为祝人长寿之词。
区区一个花儿匠,取名为“椿”,自然和他的营业有密切关系,可以寓意于他所出售的树种、花种的生长不衰,他所种植的花木均有和椿树一样的“长寿”的特质,能起一种广告的作用。
相反的,一个普通的花儿匠,曹雪芹却不可能让他以“春”为名。
这有三点可说。
第一,曹雪芹已在书中塑造了贾府四姐妹生动且令人难忘的形象,并精心地为她们起了富有深意的名字: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人都以“春”命名,其上一字“元”“迎”“探”“惜”,谐音“原”“应”“叹”“惜”。而那位花儿匠只不过是生活于贾府之外的草芥小民,他的名字在书中也仅仅一闪而过,并没有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为什么要让他的名字也镶嵌着“春”字呢?
第二,“椿”字也是曹雪芹相当熟悉的。《红楼梦》第30回的回目下联不就叫作“椿灵画蔷痴及局外”[13]吗?那个“椿灵”,以树指人,就是龄官的代称。
第三,在《红楼梦》第5回,一则曰“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二则通过判词和“红楼梦曲”,曹雪芹对封建贵族大家庭的没落抒发了悲凉的叹惋之情。一些叹惋往往是通过那个“春”字来表达的。像“春梦随云散”[14]“勘破三春景不长”[15]“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16]“画梁春尽落香尘”[17]等,无不是“春景不长”“春尽”的感伤之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还会把“方”字和“春”字连在一起,给那位不知名的花儿匠起名呢?
因此,此花儿匠之名,应以“方椿”为胜,以其他脂本一致的“方椿”为是。
推测起来,皙本的抄手或许是一时偷懒,省掉了“椿”字的“木字旁”而已。
从本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考述了皙本独异的三个人名(贾义、周氏、方春),它们之所以“异”,都与抄手的讹误有关。
在接下来的几章,还要考述另外几个有疑问的人名(红蔷、秋雯、焙茗、夏忠)。它们是不是也和抄手的讹误有关呢?
请接读便知。
[1] 此处前后出现两个“贾义”之名,现依次标注“a”“b”,以示区别。
[2] 第13回参加秦可卿丧事活动的贾府族人中,草字头一辈有“贾蔷、贾菖、贾菱、贾芸、贾芹、贾蓁、贾萍、贾藻、贾蘅、贾芬、贾芳、贾兰、贾菌、贾芝”等。
[3] 《红楼梦》第4回说:“现任族长乃是贾珍。”
[4] “周”-“冂”=“吉”。
[5] “吉”+“氏”=“袁”。
[6] 曹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初七日奏折。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初七日奏折。
[7] “孔目”是唐宋时期官府衙门中的高级吏员。《资治通鉴》“唐玄宗填报三载”胡三省注云:“孔目官,衙前吏职也。唐世始有此名,言凡使司之事,一孔一目,皆须经由其手首也。”
[8] 这位孔目姓叶也好,姓余也好,只不过是小说家笔下一个虚构的人物,若说此人和福建建阳余象斗家族有血缘关系,那根本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
[9] 参阅拙文《水浒传双峰堂刊本:叶孔目改姓与余呈复活》,载《水浒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0] 在《水浒志传评林》的版面上,分为上下两栏,下栏是正文,上栏则是“评”。
[11] “卜世仁”,谐音“不是人”。
[12] “觔”即“斤”。
[13] 参阅庚辰本、舒本、彼本、杨本、梦本。“椿灵”,蒙本、戚本作“龄官”,程甲本、程乙本作“椿龄”。
[14] 警幻仙姑之歌。
[15] 惜春判词。
[16] “红楼梦曲”第九支“虚花悟”。
[17] “红楼梦曲”第十三支“好事终”。